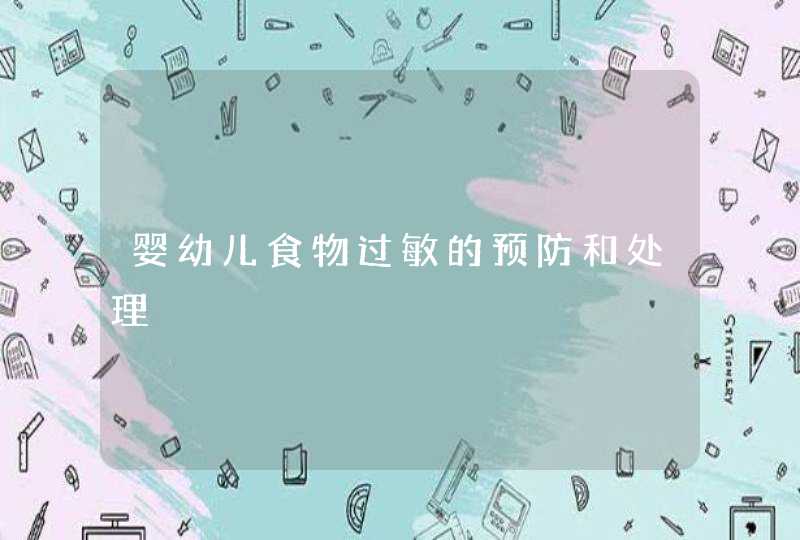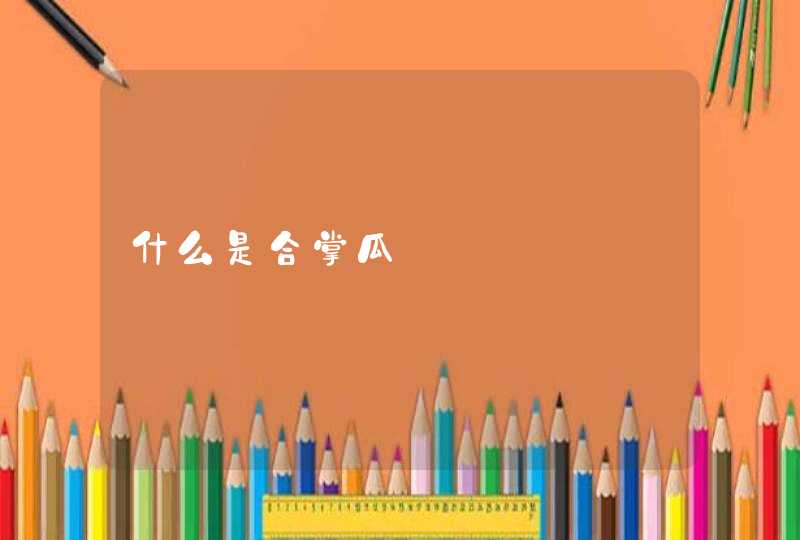南朝齐雍元年,周青写了《四声切韵》,提出平声入四声,而沈约则将四声的辨正与传统的诗赋用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创作五言诗应避免的格律缺陷。这就是后世记载的“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等等。“四声八病”在永明体诗歌创作中的运用,对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具有积极意义。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一下:
(1)平头。五言诗的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不能和对句的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同调。不然你就平头了。比如古诗“香时温润清,壶斜月台。”在《联众》中,“方”、“体”是平调,“史”、“胡”也是平调。读起来不好听。这叫平头。
(2)上尾。五言诗的第五个字(句末字)和十字(句末字)不能同调。否则,这将是一个错误。比如吴明在乐府里的诗:“绿江边草,阴园里柳。”草柳都在上声,犯了上尾的问题。
(3)蜜蜂的腰。顾名思义,蜜蜂的腰两头大,中间小。意思是一首五言诗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的声调不能相同,或者第二个字和第五个字不能都是浊音声母,第三个字是清音声母,否则就是蜂腰的问题。如蔡邕《长城洞饮马》:“客从远方来,留我一对鲤鱼。”“从”“方”是平仄字,“我”“里”是浊音字,中间的“双”是清音,所以两头重中间轻,这就是蜂腰的问题。另一个例子是沈约的《当你提前离开时,在老朋友车里的礼物》:“昨晚你住在哪里?今天早上回来。”“晨”和“归”是同时发生的,也犯了“蜂腰”之病。
(4)鹤膝。五言诗第一句的第五个字和第三句的第五个字不能同步。比如:“拨金陵朱,顺流背城门,挥太空船影,月挂山上。”如果第五句中的“诸”字是上声,那么第三句末尾的“应”字就不能在上声中重复使用,这是违反鹤膝的。再如沈约的《我不能顾邻》:“影随斜月来,香随远风来。这是知错就改的问题,想哭就哭成泪人。”第一句的第五个字“来”和第三句的第五个字“非”是一样的。也就是犯了“鹤膝病”。
⑤大云。一首五言律诗的两句话里,不能有和韵脚同韵部的词。再如,五言诗若与“新”押韵,则上述九个字中,不得有“任”、“金”、“林”、“申”、“陈”等与“新”押韵的字。如果有一种,那就是大韵。如韩乐府:“胡姬年十五,春来唯他。”“胡”与“鲁”的谐音,是一个很大的押韵问题。有些人犯了押韵的毛病,比如曹植的诗:《京味杨茁清》,就是“京”和“清”是一样的。也有在十字架内犯罪的,如古诗:“无磐石何益,虚名何益?”即“石”与“利”也。
(6)小韵。五言律诗的两句之间不可能有属于同韵部的词,除非有叠韵。如文《题山居》:“古木老树连岩,急泉清沙。”其中“舒”与“陆”,“连”与“全”是同韵,这是小韵的错。鲁《仿古曲》:“嘉树生于晨阳,霜封其条。”其中“阳”和“爽”是谐音。做一点押韵。另一种情况:叠韵,同一个字,情理上说得通,如“婉约”、“徘徊”、“徘徊”等。,但也不能算是犯小押韵的病。
如果犯了大韵小韵的病,对诗歌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如果能避免,当然就好了。如果想把文字截掉,让文字通顺,动不了,也可以避开。
(7)侧面按钮。接下来,就是声母相同的单词。如“刘”“刘”。这意味着在一首五言律诗中,两句不相交的部分不能有双音词。(两个或两个以上声母相同的词,如“公”)如五句中有“月”字,则不允许在“月”字后加“鱼”、“元”、“阮”、“愿”等字。比如:“一条鱼游起来很浪漫,一只野兽走起来怕伤了蹄子。”其中“于”与“月”的声母属于同一家族,古音存疑,使胖妞发疾。再如曹植的《又赠丁残》:“金碧辉煌的府第,美丽的城池。”其中“居”和“舒”是两个声部的疾病。
(8)正极按钮。新,就是一个字,韵母相同,但声调不同。如“流”和“长”。这是指一首五言诗的上下句中声母和韵母相同的词。比如五言诗《任》、《李》、《任》、《如》,四个字是一个新字;在一个句子中,“任”这个词已经存在,但没有“任”、“任”、“如”这样的词。比如古诗:“我是大家闺秀,我是来嫁单家的。”其中,“家”和“婚姻”这两个词,就是做出积极改变的病。
“八病”说曾经盛极一时,对促进诗歌节奏的和谐有积极意义,但过多的刻板印象无疑制约了诗人的创作。诗歌发展到格律时代,有继承也有改革。唐宋时期批判的人多,沿袭的人少。对初学者来说,知道“八病”的禁忌是有益的,但不必处处遵从。这个理论毕竟不是一个严格的规则,是可以突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