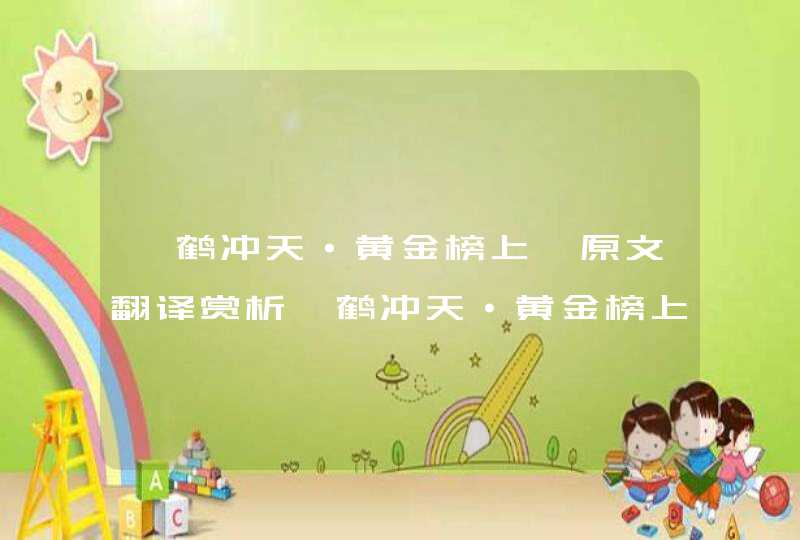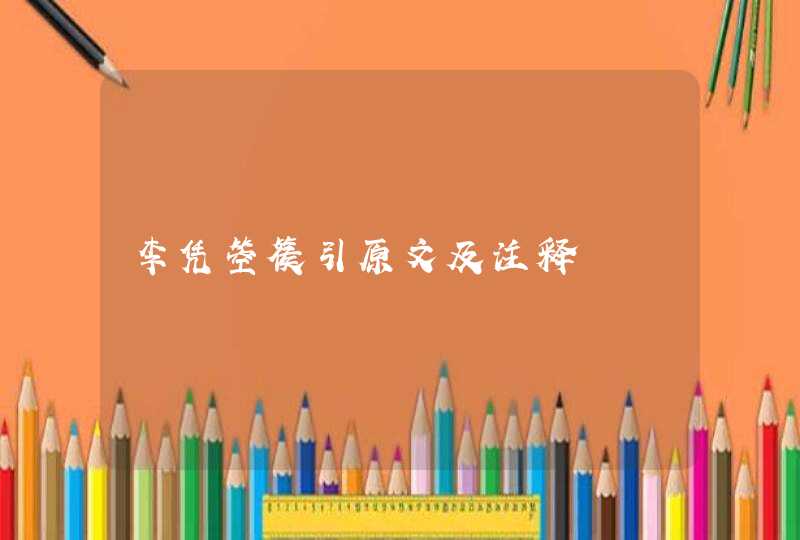在斜阳上画一角城,画一幅哀,沈园非复池台,春波绿于悲桥下。
40年后,梦已碎,沈园老柳不吹棉。
此行是山土,至今仍留有痕迹。
[作者]: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高宗时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
[翻译]:城墙上的喇叭声似乎在哀悼,沈园也不再是原来的亭子。
在那座悲伤的桥下,泉水依然碧绿。我曾在这里见过她美丽的侧影。
她去世四十多年了,我做梦都见不到。沈园的柳树和我一样老。
连柳絮都不见了。我已经七十岁了,快要死了。我仍然来这里哀悼和哭泣。
城墙上的喇叭声似乎在哀悼,沈园也不再是原来的亭子。
在那座悲伤的桥下,泉水依然碧绿。我曾在这里见过她美丽的侧影。
她去世四十多年了,我做梦都见不到。沈园的柳树和我一样老。
连柳絮都不见了。我已经七十岁了,快要死了。我仍然来这里哀悼和哭泣。
这是陆游七十五岁重游沈园(绍兴)时写的一首诗。
三十一岁时,偶然遇见被专制父母分隔的前妻唐婉,题写钗头凤题壁,以记其苦念与深仇。没想到,这一面成了持久战术。晚年,陆游多次到沈园吊唁。这两首诗是他悼亡诗中最深刻、最感人的。
诗的开头用夕阳和彩绘的管乐器画角,把人带入一种悲凉的世界意境。他去沈园寻找曾经有过痕迹的老池台,可是连池台都认不出来了。这成了唤起痕迹的记忆或幻觉的一种罕见的希望。这座桥是一座悲伤的桥。只有看到桥下绿水,才觉得这一次是春天。因为桥下水了,我曾经像曹植的《洛神赋》一样看到了凌波仙的倩影。可以说,沈的潜意识是在寻找青春的幻觉,而他所找到的是美的瞬间性。
第二首歌以第一首歌《惊现赵鸿英》为背景,询问红英现在何处。
“香消玉殒”是古代美人之死的一个优雅比喻。唐婉去世已经40多年了,寻梦或者幻觉的行为已经成为生者和死者之间的精神对话。在生与死的对话中,诗人有荒原老了,人老了的感觉。甚至那些曾经在春天装点城市的沈阳柳,也已经老得不再在春天绽放。美人早就“玉骨已埋春”,幸存的老骨头老得化不成会稽山(今绍兴)的土了。但是,一条情感线的不断切割,让他来到沈园寻找痕迹,流下了眼泪。
梁启超在读陆游悲壮激昂的爱国诗时,曾称他为“一个永远的人的解脱”。没想到,沈渊的诗,说明这个天长地久的人,也懂得爱孩子的趣味。他甚至在自己被毁掉的初恋中,在自己有缺陷的人生经历中,年复一年地体验着生命的青春,对自己的晚年依然忠贞不渝。如果说“钗头凤”这四个字还没有忘记昔日的海誓山盟,心中还有珍贵的锦书,隐隐散发着生命的热量,那么我们在经历了凛然的空灵空灵的表象时,就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极限。在生命的极限,爱在捍卫自己永恒的价值,这是沈园第二首诗留给后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