柠檬的
《大智慧论》中有一个鬼故事,后来在佛教文献中被称为“两鬼争一尸”。这是忒修斯之船的思想实验的东方版本,包裹在一场关于有我无我的哲学辩论中-
问:
你为什么不认识我?
每个人靠自己谋生,而不是靠自己;如果他自己没有自我,他把自己看成是我,他也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我。
回答:
这就难了!
在别人身上谋生,就要说“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上谋生”。
第二次以后,五公因缘空无我,从无明,生于二十身。是我的自我意识在五阴相之后诞生的。从此五人相生,即五人为我,不在他人,习以为常。
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上帝,也可能有另一个。如果你有什么未完成的事情,问我!当一个犹太人问兔子的角时,他的回答像马的角。如果马角是真的,可以证明兔角;马的角还没完成,但我想证明兔子的角。
第二次以后,自从我出生在我的身体里,我就称自己为上帝。如果你一直说上帝,你也应该把他算作我。所以,我们不应该说自己活在自己心里,而不是活在别人心里,所以我们知道有上帝。
再一次,有人在其他事物中诞生在我的脑海中,比如一个佛教禅修者。我以地见万物,我见地,我即地,如水、火、风、空。所以,倒过来,他也把我算在他的身体里。
一次又一次,有时候我是他生的。如果有一个人,我被送去远方旅行,独自留在空。半夜,一个鬼在前面抬着一个死人,另一个鬼跟在后面,骂着前面的鬼:“如果是死人,是我的东西,你凭什么抬?”鬼魂先说:“这是我的东西,我还抓着不放。”鬼说了一句“我要对死者负责!”两个鬼各为其争。鬼说:“有人问。”说完,鬼又问:“死人谁负责?”是人的思想:“这两个鬼力量大,真的就该死,假的就都该死。什么是假的?”语:“鬼来之前。”鬼大了以后,捕手抽出手,落在地上,而鬼拿死人之前,一只胳膊就能够着。如果是两只胳膊,两只脚,头和侧面,很容易抬起来。于是两个鬼一起吃了饭,换了身,擦了嘴就走了。他心想:“我妈生下来,我看见两个鬼吃光了,现在满身都是他的肉。我今天有自己的生活,不是吗?没有尸体吗?如果是,都是他的问题;不以为然,今日有体。”如果你在思考,你会很无聊,比如一个疯子。到了明朝,我找到了去前土的路,在那里我看到了佛和和尚。不管我还做了什么,我问自己有没有事做。和尚问:“你是谁?”回答:“我连自己是人都不知道。”也就是说,要为所有的僧人说事。诸比丘曰:“此人自知无我,易得之。”俗话说:“你从一开始就来了,从来没有自足过。不适合今天。但以四大和为我身,如己,与今无异。”诸比丘度是道,诸烦恼断,即阿罗汉。
因为有时候他也算我的。你们不能拥有彼此,所以你们有我。
这部名为《大智慧论》的经文,被视为东亚大乘中庸派最重要的四大经典之一。中国古代僧人认为是印度庸人学派创始人龙树的作品。但它的梵文原文没有一行流传下来,藏文和梵文文献中也没有关于它的记载。关于这部经文的翻译,我们可以从鸠摩罗什同时代人的叙述和后来的传记材料中得到以下信息:大约在402年至406年间,应秦朝末代皇帝姚兴的要求,鸠摩罗什在长安名为逍遥院的翻译局的500多名助手的帮助下,将这部梵文经典翻译成中文。在《大正藏》的印刷本中,我们发现了对其梵文标题更为贴心的翻译:《论大乘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解读。在库车(鸠摩罗什的诞生地)发现的一些手稿残片,用汉语将其梵文标题音译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有波多特莎”,表明它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的一部“有波多特莎”,即问答形式的注释。同时,这些手稿碎片也表明,这部经文的一些内容可能在鸠摩罗什开始他的翻译项目之前就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但是,《大智慧》是第一部“完整”的中文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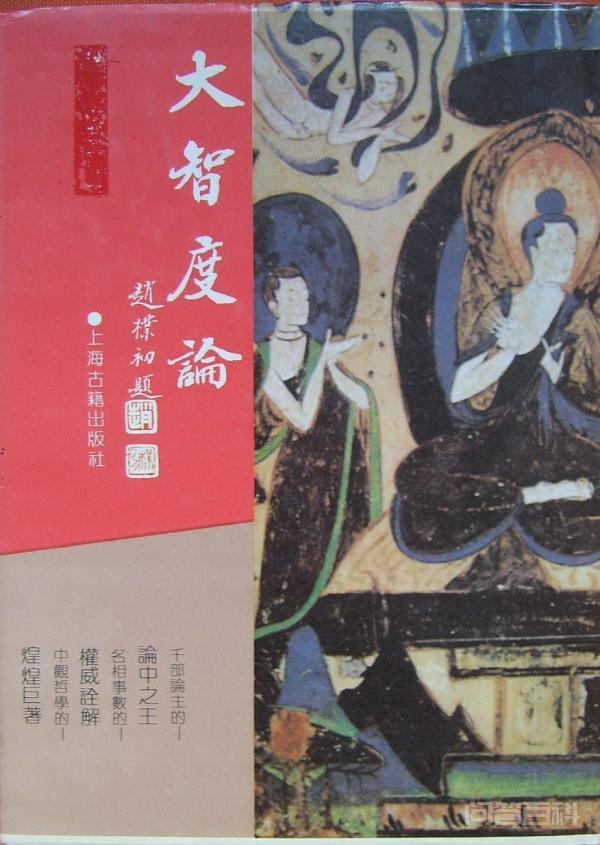
《论大智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鸠摩罗什享有忠实翻译家的美誉。据说他临死前发了一个诚实的誓言,如果他的翻译没有偏离梵文原文,他的舌头将能够承受火葬的火焰。当我们在传记材料中读到鸠摩罗什对原作的忠实在对骨灰的检查中得到证实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这个传说自然很动人,我们也相信鸠摩罗什尽了最大努力避免翻译错误,但有证词证明,他为了迎合中国读者对简洁文学品味的偏好,大幅删减了梵文原文。在《大智慧论》中,不仅有一些明显针对非印度读者的印度习俗解释,还多次提到“秦言”,即汉语,这让学者们怀疑鸠摩罗什和他的中国助手可能相当自由地干预了文本(他们所服务的读者远比现代读者更具世界性)。虽然《龙树》通过提示名家代表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论点,解释了书中各种规律的“总貌”与“异貌”的区别(这些读者似乎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鉴于这些“可疑”的因素,这一文本的起源成为争议的主题就不足为奇了。学者们已经确信这不可能是鸠摩罗什所说的龙树的作品。一些研究人员走了极端。看来他们是想把一部对东亚佛教影响很大的著作《大智慧论》做得更“东亚化”。据推测,它可能是中国作品,也可能是鸠摩罗什本人伪造的。然而,这段文字包含了许多线索,导致其他人坚持认为这部佛经是在4世纪初写的。原文是梵文,是中亚佛教高僧团成员,或者皈依大乘佛教高僧团成员写的。尽管我们所拥有的单薄的历史证据不足以解决其起源问题,但书中散落的中国元素似乎更像是鸠摩罗什为该书的新读者量身定制梵文原文时添加的,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质疑他的翻译工作的500位见证人的诚实性。但他在临死前的誓词中提到了自己的舌头,这表明了另一种可能:由于他经常向助手们口述翻译,并在口述过程中向他们解释原文中的各种难点,所以他对原文的口述注释可能已经被编入了这些助手们所写的《大智慧论》。法国汉学家戴米未曾警告说:“鸠摩罗什的注解太多了,人们永远不知道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梵文原文。”
回到前面引用的故事。为了向他的论证对象解释一个人可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看到一个“我”,故事的讲述者举了这个故事作为例子。故事讲的是一个旅人晚上睡在空的房间里,半夜突然闯进来两个鬼,为了抢一具尸体互相争吵。旅行者被要求决定尸体的所有权。当他老老实实把尸体颁给第一个抬尸体的鬼时,第二个鬼勃然大怒,把他的身体各部分都撕掉了。第一个鬼魂不停地用尸体的相应部位修补自己残缺的身体。最后,当人的整个身体被替换后,两个鬼魂一起吃掉了旅行者散落的四肢,扬长而去。主人公已经忘记了他现在是谁。
这个故事很可能不是《大智慧》作者原创。和这本书里的其他一些寓言一样,它似乎来源于公元二世纪阿育王的一部梵文传记,只有部分文字流传下来。我们这个故事的前身梵文原文已经失传,但这个前身幸运地保存在中文版的《阿育王传》中。传统上,这本书被认为是梵文阿育王传的直接中文翻译,它写于4世纪初。《阿育王传》专门讲述阿育王的老师优博多多的生平。他的主要成就是指导了很多弟子成为阿罗汉。其中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年轻弟子想要回归世俗生活。优博一多意识到这个弟子对自己的身体有很深的依恋,于是决定从字面上切断这种依恋。在去年轻人家的路上,他的主人在晚上来到他面前,伪装成一个女巫,带着一具尸体。然后是第二个夜叉,也是悲浪幻化的产物。在两个女巫用一具尸体代替了他的整个身体之后,这个年轻人——故事的叙述者希望我们相信——立刻消除了他所有的执念。这个故事并没有提到由此引发的任何痛苦、困惑或追问。相反,它匆忙地以一个简短的描述结束:年轻人回到他们多灾多难的家园,成为罗汉。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阿育王经》中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据说是由梁朝僧人僧伽婆罗多翻译的。这里有两个罗刹,像夜叉一样,吃生肉的鬼。当第二个罗刹抓住小伙子的胳膊时,第一个罗刹迅速往反方向拉,防止胳膊被拉断。两个罗刹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抓着小伙子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朝相反的方向拖拽。最终,这个人活了下来,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却完好无损。对于后来的读者来说,原著中那个年轻人的身体被他帮助的第一个鬼魂吃掉的情节似乎总是一个问题。《阿弥陀佛经》的作者窥基也改变了情节。他说,第二个鬼魂(据说更年轻或更大)咬掉并立即吞下了这个人的四肢,而第一个鬼魂(被描述为比第二个鬼魂更老更小,暗示它无法阻止第二个鬼魂的暴行)感到内疚,因此必须用尸体的相应部分替换它。



中国台湾省艾达电视公司录制的歌剧《妻后幽魂》改编自《大智慧论》中“两鬼争尸”的故事。
将这位旅行者的故事与《阿育王传》中的前一个故事并置,无疑会帮助我们理解故事叙述者的担忧。但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故事的最后一幕。这个变体重复了离开-转变-返回的结构模式。对于一个有着诸多烦恼的弟子来说,回归师傅已经显示了他的觉醒,而我们的主人公却在一种深刻的困惑中回到了“他的故土”。在他的文字和象征性的旅程结束时,他遇到了一群僧侣。当他问自己是否还有肉体时,他们评论说,他正确地否认了有一个“我”在肉体的替换中幸存了下来。为了帮助他走向觉醒的最后一步,他们告诉他“我”并不存在,“不只是现在,而是从一开始”。他们的语气严肃而肯定,但他们提供的似乎是值得怀疑的意见。当我们的主人公说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否还是人,更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他似乎预设了一个“我”的存在,尽管他并没有反思“我”是由什么构成的,他所乞求的只是确认自己与新身体的联系。然而,僧侣们似乎错误地认为我们的英雄说他知道现在说话的不是他。虽然故事的叙述者把这些僧侣当作他的代言人,但他奇怪地允许他们传达一个明显与他自己对旅行者经历的描述相冲突的信息。正如他在谈话的最后再次强调的,他自己对这个故事的解读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找到一个“我”是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更亲切、更详细的方式来理解僧侣们的指示。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那个有着诸多忧虑和波澜的版本中,弟子在看到自己幼小的身体被摧毁时,似乎并没有感到任何痛苦,尽管他在片刻之前还极其珍惜这个身体。第二天早上,他的醒来伴随着阳光自然而来。要理解这种不正常的表达,我们需要看到,这个故事和《阿育王传》中与之相邻的其他故事都旨在传达一种朴素的禁欲主义理想。事实上,把自己的身体看做一具尸体是很多悲浪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显然与僧人的一些禅修做法有关。他们试图通过可视化身体的各个部分,进行解剖分析,以及可视化不同阶段的尸体(这一传统今天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来反映他们身体的腐烂和不洁。
大智慧的叙述者,作为很多故事的读者,很可能会被年轻人的反应困扰,就像我们被它困扰一样。与《阿育王传》的版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智慧论》中的版本清楚地将身体的替换描述为降临到主人公身上的不幸。在令人不寒而栗、面带微笑的吞食尸体的场景之后,出现了一个以其全部情感重量击中我们的图像:在一种绝对的孤独中,我们的主人公开始思考他的经历,这些经历超出了人类经验的极限和他以前对自己的理解,这种不理解几乎使他变成了一个“疯子”。在这里,叙述者用“他的头脑混乱”这个短语来描述这个人的经历。它不仅指“他的心是混乱的”,也指其他佛教文献中所显示的一种极端的身体痛苦。借助鸠摩罗什无情的舌头,叙述者告诉我们,旅行者在极度的痛苦中默默地寻找回家的路。叙述者(不同于他的故事的现代译者)认为这比继续前进更现实,与僧侣的相遇使旅行者恢复了与人类的交流,进而使他最终的解放变得可以理解。
熟悉佛教寓言的读者会惊叹于叙述者在这里的巧妙手法。在这些故事中,感到“无聊”的人往往被描述为要么像流浪狗一样四处游荡,不知道该去哪里,要么一头栽倒在地。所以,在旅者艰辛的归程中,在他努力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一样站起来的过程中,有着更深的痛苦。我们还需要记住,叙述者可以合理地期望他的读者认识到贯穿这些场景的主题:有人因为某种原因陷入了存在的困惑,一位导师出现了,引导她/他走向觉醒。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大智慧的故事中,僧侣的出现并不是为了传达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哲学教导,而是为了满足一个主题功能,那就是给受难的主人公一个快速的解脱。作为一个机械神,他们不仅把被抛弃的无名之人,活人的身体送回了人类世界,还把他带入了一个神圣的群体。虽然通过教导来拯救受害者是佛教寓言中常见的主题,但我们不应怀疑它包含了叙述者的真诚关注。他在出于自己的哲学目的而借用了许多《伤逝》和《惊涛骇浪》的故事的同时,伸出手,用许多《伤逝》和《惊涛骇浪》中所缺乏的温暖,给了我们的主人公和被古老的悲伤穿透的读者一种形而上的安慰。毕竟,根据《大智慧》的作者,他的教义的核心在于慈悲。而我们故事的叙述者显然希望他的英雄之旅的终点也是他的读者之旅的终点。
编辑:郑世良
校对:蒙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