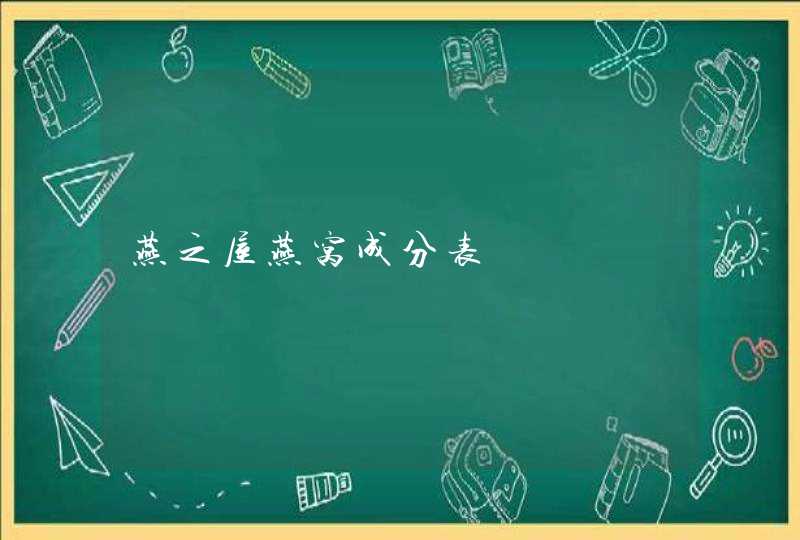近日,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参加了中国财富管理50人青年学术论坛举办的“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政策空与传导效应”专题研讨会,就如何平衡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了点评。高善文博士认为,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认真考虑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基本问题是,目前的中性利率是什么水平?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第二个基本问题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是否正在发生范式转变?他强调,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货币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做好应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前瞻性理论准备和政策储备。
以下为发言汇编。
我想重点讲两个方面,补充今天的讨论,梳理一下货币政策工具的基本问题及其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价格工具分析。价格工具主要用于确定金融市场的资本价格。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被忽视但又极其关键的问题是:在给定的金融市场中,中国的中性利率是什么水平?中性利率是否显著下降?中性利率及其变化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提供了参照系。只有基于这个参照系,才能知道货币政策是松还是紧。但目前所有的讨论中似乎都隐含着一个假设:中国的中性利率总体是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忽略中性利率,直接判断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
这个假设有很大的问题。过去十年中国的中性利率稳定吗?未来十年会变到什么水平?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那么确定。其实我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中性利率在下降,尤其是2018年以来。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中性利率将出现显著下降。
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从三年前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利率水平可能是略有宽松或者基本合适的;但中性利率下降后,目前的利率水平可能会明显偏紧。因此,研究中性利率的变化对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似乎还不充分。
为什么中性利率在下降?有学者指出,目前的加权利率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暗示货币政策非常宽松。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经济增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即使扣除疫情影响,近两年的增速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低点。通过对各种口径的企业(包括工业企业、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的研究,以及对增量资本产出率和经济整体资本回报率的估计,清楚地表明,实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处于历史低点,特别是近十几年来。
因此,从历史平均水平来看,目前的利率水平可能是宽松的;但如果考虑到同期中性利率的加速下降,那么目前的利率水平也可能是偏紧的,至少不会像简单比较暗示的那么宽松。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整体面临易热难冷的问题。信贷扩张和经济扩张的支撑主要来自于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然而,自2010年以来,经济整体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始终处于疲软状态。由于私人部门信贷需求不足,过去十几年支撑经济最重要的动力是基建和房地产,大量新增信贷流向这两个领域。
但这种融资需求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政府基础设施融资一般被认为有政府隐性担保,严重扭曲了价格;第二,出于土地财政、金融稳定等因素的考虑,房地产融资也被认为具有某种形式的隐性担保,与整体经济稳定密切相关。
在过去十几年的实践中,每次房地产市场走弱,政府都会积极救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房价的通胀预期和房地产市场刚性兑付、预算软约束的预期。预计这将导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部门以异常高的利率融资,并挤出私营部门。由于这种扭曲,这一时期的中性利率可能会被系统性扭曲,并被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2018年之后,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是政府融资平台受到限制,地方政府变相加杠杆和隐性债务基本得到控制;二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三条红线”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去杠杆化进程,导致大量房地产企业违约,房地产市场在供给侧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清理。
直接结果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的资本需求大幅萎缩。在这种背景下,整个经济对增量资金的需求正在快速萎缩,之前出现的市场扭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纠正。如果疫情叠加,目前的中性利率必然会比2020年前大幅下降。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信贷需求不足的关键解释是当前的政策利率过高,甚至可能高于中性利率,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紧缩效应。
在研究利率时,我们必须将中性利率纳入研究框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从过去十年到未来十年,中性利率会发生巨大变化。
以美联储为例。2010年以来,美国剔除通胀后的中性利率约为0 ~ 0.5%;但2000年以前可能在3%左右。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2008年,美国的中性利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当时美联储对它的认知是相当模糊的。当时,无论美联储如何加息,远期利率都不断下跌,非常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与金融海啸的爆发密切相关。2010年后,美国的中性利率持续下降,基本接近0%的水平。至于2020年后美国的中性利率是否会上升?对美联储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见,不研究中性利率的合理水平及其结构变化,去分析货币政策是松还是紧,去研究采用哪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都有些漫无目的。
第二个问题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范式转变。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对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和框架的影响不容忽视。
虽然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很多,但在2007年之前,私人部门信贷是我国货币政策最主要的传导渠道。如果想要货币紧缩,最有力的手段就是使用信贷控制。只要私人部门信贷被掐,经济很快就会降温;只要私人部门信贷稍微放松,利率稍微下降,过一段时间实体经济就会反弹。因此,在2007年之前,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是信贷,最主要的手段是信贷规模的控制和利率的控制。
从2008年到2021年上半年,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变成了基建和房地产信贷。社会融资和表外融资不断大起大落,虽然背后有货币当局的影响,但更多体现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扩大经济的努力。
每当地方政府扩大基建,加速隐性债务积累时,银行端的社会融资规模就会急剧上升;当政府鼓励房地产时,银行对房地产信贷的需求也会迅速扩大。
从金融体系来看,这种传导机制与2008年之前类似,不同的是信贷需求的主体从私人部门变成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市场。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这种传导机制与之前并无本质区别,都是通过扩大银行的信贷账户(或表外信贷)来实现的。
但目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经基本得到控制,房地产信贷可能在放缓。在这样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出发点在哪里?如果地方政府、房地产、私人部门不进行融资,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是什么?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依靠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来推动增长。毫无疑问,这些行业对信贷的需求强度和提供合格抵押物的能力与传统行业有很大不同。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正在发生范式转变。在这种背景下,继续基于传统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和思路来研究问题,可能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比如信贷渠道被堵住了,货币政策会不会没有传导渠道?绝对不是这样。日本早就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房地产市场积累了巨大的泡沫。日本银行的利率早就降到零了。日本的货币政策不能影响经济,没有传导渠道吗?
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安倍的“三支箭”。虽然他未能实现将通胀推回2%的目标,但显著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复苏,通胀也有一定程度的回升。20世纪50-70年代,日本货币政策的传导主体也是信贷。安倍“三箭”时期,汇率成为最重要的传导渠道之一。此外,股价大幅上涨,财富效应也是重要的传导渠道。由此带来的预期和风险偏好的变化对资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资产价格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而这在日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不是主要渠道。
看看美国的情况。近二十年来,美国的中性利率持续下降,甚至逼近零利率。在这种背景下,无论美国如何降低利率,私营部门投资普遍疲软。利率下降刺激了房地产市场,催生了很多创新的金融产品。金融海啸后,房地产泡沫被戳破。在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下,私人部门投资并没有明显加强。美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载体也依赖于资产市场(包括债券、股票、房地产市场等。)和汇率市场,虽然信贷渠道始终存在,并与其他渠道相互作用。
因此,在私人部门信贷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仍然可以有效地影响经济,但其发挥作用的渠道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政策工具。
综上所述,我建议你研究一些更基础的问题,这对理解当前的政策困境和设计未来的政策工具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回过头来看我刚才讲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是目前的中性利率是什么水平?朝哪个方向?从历史角度来说是什么水平?二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是否正在发生范式转变?面对这种范式转变,货币政策在操作层面的重心是否也会发生变化?工具需要换吗?
随着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货币政策应与时俱进,做好相应的理论准备和政策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