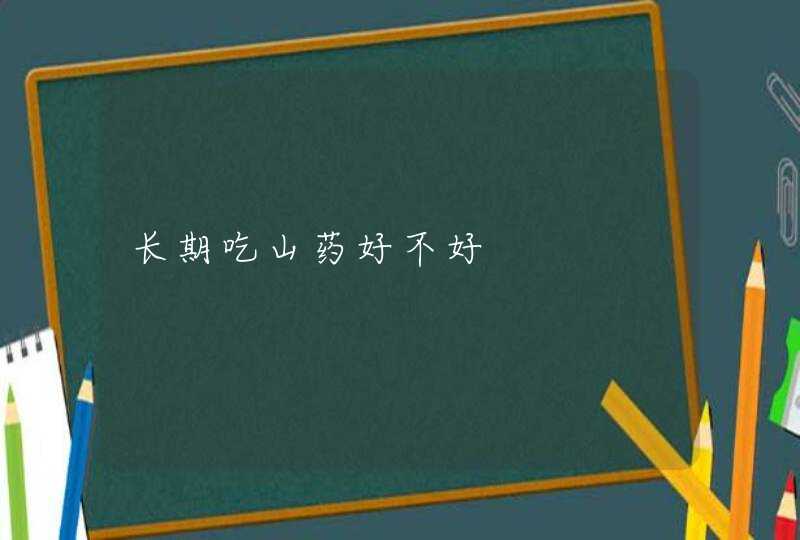在食物链中,处于顶端的生物越多,下游链受到的影响就越大。二旗生态的核心,无非是大厂和员工。公司人少,司机也不来。现在在群里卖草莓的女人,已经搬到了二旗地铁口附近的人行道上,支起了一个小台灯,“两盒15元”。腾讯门口卖盒饭给司机的阿姨也不见了。五月的一个中午,陈大强饿了很久,终于在一个蛋糕摊上吃到了午餐。
身处共生体系,大厂的日子不再轻松,司机们也在适应新常态。
西二旗的夜晚很安静
在自然界,微小的生物常常依赖于一个巨人。例如,牛椋鸟经常与犀牛为伴,啄食犀牛背上的寄生虫和昆虫,还为视力低下的犀牛充当“哨兵”。
这是一套互利共生的规则,就像西二旗没有自己的司机一样。严格来说,司机不会一直待在西二旗。只是他们提前从晚上九点到凌晨一点从北京的各个角落赶来——这个时间最好控制在八点半左右。太早会浪费等待的时间,太晚又抢不到好座位。所以晚上9点以后,王璐西北、软件南街和后厂村路就像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哨声、吼声、脚步声、谈话声混杂在一起,迎来了中西第二面国旗最受欢迎的时刻。
西旗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的所在地,百度、腾讯、滴滴、网易、新浪和快的都将总部设在这里。二旗也是北京人流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仅在二旗的地铁站,每天就有30万人在此乘车,比春运高峰期北京西站的车流量还大。乘务员平均每个月都会捡回遗留在站台下路床上的20多双鞋子和70多个背包挂件。
第二面旗也支持司机陆斌的家庭。他今年53岁。中年下岗后,他经历了一次创业失败。他卖掉了进口帕杰罗,买了一辆现代主导的汽车来经营网络。西樵的人流量一年四季不断,互联网厂商的加班报销制度为司机提供了上千的固定订单。任何一个家住西二旗的司机都知道大厂的规矩:百度九点以后打车,腾讯九点半打车,Aauto快一点十点打车。一个聪明的司机会在10点半之前全速回来,因为这个时间又是一波工作。如果他足够努力,可以等到凌晨一点半的最后一个小高峰。
吕斌至今忘不了西二旗晚上打车的盛况。一个接一个,长途预约单的铃声一次次响起。他和他的车从来不停下来,绕着外环转。乘客一上车就宣布手机尾号,一踩油门就出发了。跑一晚上,流水能花三四百。
现在,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今年2月以来,腾讯、阿里、百度、字节跳动等头部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裁员了。许多司机告诉人们,他们在西二旗的单量比过去少了30%。他们开始有了闲暇时间,有时会把车停在路边,左手撑着驾驶座的车窗,刷刷短视频,打打游戏,甚至干脆把座位放低,直接把腿搭在前窗。
从4月底开始,大量的互联网公司都在家里办公。用陆斌的话说,“西二旗的声音降了几十分贝”。本来打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如果忘记预约,大厂员工下班要排队等一个多小时。现在,在西二旗的任何一个角落,无论单子多小,几秒钟内都要有人接单。
晚上九点,车辆摄影在百度|钟楼下等候
“大买卖!晚上九点半,第一辆汽车的一名司机看见了我,急忙穿过马路,在公共汽车上迎接我。从Xi的二七地铁站到百度大厦,1.5公里的距离,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财神不在,那你连饭都吃不上。」
司机和我一起下车,他准备在百度大厦外等下一单。这里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个司机,等了很久才让他们下车聚在一起聊天。话题无非就是他们今天接了多少单,什么时候回家。从远处看,西装革履的司机们皮肤都很黑。走近了才发现,他们大多又老又累,白衬衫从裤带里扯出来,挂在多年来肿胀的肚子上。
就像牛鸟和犀牛的关系一样,在这个由互联网诞生并构建的体系中,数百名司机分享了互联网公司下班所需的巨大运力,也从中获得了很大一部分收入。他们是互联网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裁员之后,司机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大厂和员工的变化。陆斌发现乘客越来越沉默,不爱说话。有时候陆彬会试探地问:“今天天气真好。”过了几秒钟,后座才传来“嗯”的一声。即使有乘客开口,也是源源不断的苦水。百度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员工向他抱怨,在他的单位,“领导也是他讲课选对象。”他有家有口有房贷,每次都是第一个被领导训的。“就拿我出气吧,”那人在他身后哽咽道。
司机李想,有一次把车停在阿auto快一点的楼下,接到一个提着行李箱的女孩。他下车想帮她提行李,她一怒之下甩开了,行李箱直接砸进后备箱。“怎么了,姑娘,回家吧?”他问女孩,对方泪流满面。原来她被解雇了。“这是她最后一次来公司。”
“想回家就回家”
在陆斌的印象中,大厂人对裁员没那么紧张。
2020年,陆彬从Xi二七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接手了一个住在旧宫的年轻人。陆斌看了一眼手机,问:“你怎么住那么远?”对方短时间内告诉他不用来了,“我下岗了”。
起初,他很生气,尖锐地指责公司的战略问题。男孩是项目负责人,项目原定4个月完成。因为前几个部门误工,他到这里的时候只剩不到一个月了。“我是背人!”尖锐的声音吓得卢斌一激灵。
但当话题离开工作时,他的语气很快缓和下来。在这次裁员中,他获得了N+2的补偿,近20万元,“好像突然有了拆迁的感觉”。身边的同事发现后,都抢着问他“指数怎么来的”。至于出路,自然不用担心。他的身体伸展在座位上。“就换下一个吧。我已经打听过了。Aauto Quicker里的福利比我们好,我就让朋友推一把。”从长远来看,他得到了更好的工作,他的朋友得到了内部晋升的奖金。“多好的事啊!”他摸了摸自己的手,打了一掌。
以前互联网公司跳槽相当频繁,再加上市场上普遍存在的薪酬倒挂现象。跳槽是互联网员工加薪的常用手段。曾经处于扩张期的互联网公司也愿意吸纳大量有经验的行业人才。那时候HR们也会为一个招聘指标而纠结。
有一次,一个大厂HR上了陆斌的车,开始打电话,“至少40分钟”。HR在车上通知了一个女生,通过了复试,尽快去公司报到。但姑娘想推掉邀约,又不想因此得罪人,一直含糊其辞的回答。他们两个就来不来的问题拖了40分钟。“当时听腻了,HR的职业道德真的很好。陆斌说。
电话挂了,最后也没有结果。陆斌立马夸HR:“姑娘,你真有耐心。」
“哦,主人,我忍不住好久了。我早就想发火了。”HR向吕斌抱怨。她自然知道对方是在搪塞,但是这个女生的指标已经上报给领导了,现在进退两难。“我以前说过我能来,但现在我不会来了。我该怎么解释呢?」
两年来,陆斌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就业市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丢了工作又担心前路的人,有保住工作危险的人,有厌倦加班又不敢离职的人,不停地上他的车。HR也成了人们口中的“冷血”角色。
今年3月底,一个蓝色光标的女生凌晨撞了陆斌的车。在他的印象中,没有多少广告公司下班这么晚。一问才知道,姑娘们准备跳槽去JD。COM的产品推广部门。他们已经收到了offer,工资也涨了50%。“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但是到了3月中旬,HR突然打电话给女孩,让她“等等”。这就是10天。JD.COM也开始裁员。再次收到HR的信息,没有HC(岗位)。
“那我为什么下班这么晚?我得抓紧时间。”本来她的下一份工作就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她根本不用太在意现在的工作。”但现在,她失去了下一份工作,只能拼命加班来获得安全感。
一名互联网员工在地铁口临时做围栏|钟图
司机们也发现,大厂的财富不如从前了。首汽约车司机王福在提到阿里和美团裁员时,立刻做出了判断。“我觉得美团裁员比较多。”司机有个行话叫“美团街”,在美团总部下面一公里长。美团的写字楼满大街都是,“9点到11点都拉不动”。现在王福发现这条街比阿里周边宽松多了。“但是阿里的估计不如以前了。”王福发现,阿里已经取消了与首汽的组织合作,选择给员工每月1200元的交通费,“想回家就回家。”
其实1200元的交通费根本不够大厂员工加班打车的钱。并不是都住在公司附近,大厂有大量员工都是远在房山、顺义、大兴买房。“这种大单子,我们得赶紧去200元。王福说。
阿里也不例外。百度也在改变方法降低运输成本。陆斌最近接了一个百度男孩,从对方那里得知“现在百度已经把滴滴列入汽车目录”。以前百度只和首汽合作。首汽作为专车,成本相当高,同样的路程比滴滴贵一倍。“但是我们打车方便多了,选择范围也广。”对方说。
当我们听到我们在谈论运输成本时,另一位首汽约车司机陈大强突然插了进来。“其实阿里并不是完全取消,还有少部分部门仍然和我们保持合作,比如蚂蚁金服。”他和一个阿里的男孩住在昌平的一个小区里。每天晚上10点,陈大强挂断了家庭模式,因为地址是最好的匹配,他每次都能被满足。交谈中,陈大强知道对方在蚂蚁金服工作,在此之前是华为的一个小领导。他“很勤快”,十次有八次在后座低头敲电脑。
一来二去,陈大强和这个年轻人达成了默契。如果他碰巧在城里,他就不会在晚上回到Xi的二七去接受命令。他一踩油门,直接开到望京的阿里。“我要等这个年轻人,带他回家。”
被感动的生活
数百年前,Xi旗还是一片荒地。为了抵御外敌,明政府向周边驻军提供战马,并将其建成牧场。后来,这个牧场发展成了一个村庄。直到十几年前,曾经进驻中关村园区的企业开始了自己的迁移之旅。土地丰富、地价便宜的Xi二七开始受到互联网公司的青睐。相传当时还有一个原因,“西二旗风水好”,后厂村是北京的迎风之地。无论谁想来这里,都一定会有很大的机会。
伴随着这个传说,Xi尔旗逐渐成为中国互联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Xi尔旗从未独立存在过。除了钢筋水泥,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生态,把分散的周边企业、员工、司机甚至整个后厂村紧紧包裹在一起。
在食物链中,处于顶端的生物越多,下游链受到的影响就越大。二旗生态的核心,无非是大厂和员工。公司人少,司机也不来。现在在群里卖草莓的女人,搬到了二旗地铁口附近的人行道上,支起了一个小台灯,“两盒15元”。腾讯门口卖盒饭给司机的阿姨也不见了。五月的一个中午,陈大强饿了很久,终于在一个蛋糕摊上吃到了午餐。
西岐地铁站外现场摄影|钟
身处共生体系,大厂的日子不再轻松,司机们也在适应新常态。
起初,这种适应是困难的。司机习惯晚上拿长途票,在这么宝贵的时间里,没有人会浪费时间纠结短途票。但是现在大单很少,但是习惯很难改变。对于任何一个车手来说,做出妥协都是极其困难的。他们宁愿花时间等待很长时间。
在百度和西山一院之间的西北王东路,司机们又聚在一起聊天,把手插在口袋里,踢着路边的石头。他们经常设置两种模式。如果系统自动派单,会划定接单范围——这个距离一般在20公里左右,另外就是预约单,比手速还快。预约单一出现,听音大厅就会迅速给出“滴滴”的提示,还会出现一个跳动的红圈,上面显示着乘客的起止点,而司机要做的就是疯狂点击。
年近60岁的陈大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但他总能在看似悠闲的人群聊天中,果断挑出耳朵和眼力,听铃声,看手机,点击抢票。“这是一种应激反应”。
离得越近,抢单越快,不同大厂抢单规则也有差异。腾讯的单子也要抢。“很多司机手机上都有插件。”陈大强年纪更大。他看不懂外挂,也打不过年轻人。不管他的手指有多快,他根本打不过机器。百度的列表是系统自动调度的,但也要看距离远近。9点前,东、西、北、南四个靠近的开口都被堵住了。
以前有时候汽车鸣笛声太大,西山一院的居民就会报警。警铃一响,哨声立刻消失,只剩下系统自动发出的“滴滴”声在街上循环。这个时候,任何一辆车不在车位上,都会被罚款。有些没下车的司机马上就走,轮到司机倒霉了。“双向街道根本无法容纳高峰时间的车辆。如果我们停得太远,我们就抢不到单子了。况且乘客位于此处,车多,我只能停在此处。”陈大强说。
但现在,在听听堂,百度和腾讯的订单加起来还不到50单,却有169辆等待的车辆。一望无际的黑色车辆堵在街道两旁,等待时间越来越长,看起来像蜂窝一样的系统红色热力图越来越弱,司机们开始焦虑。有些人注定要被淘汰。陈大强从8点等到了11点,从站着到蹲着,最后干脆坐在了人行道边的草地上。互相聊天的司机越来越少了。有些人很幸运,拿起账单就走了。"账单白付了。"有些人无法忍受无休止的等待,所以他们决定早点回家喝一杯。
出租车司机赵峰和互联网公司签约的机构司机比起来,就像个局外人。他早早八点半下楼百度。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网约车集团。他无法参与第一个专车司机的聊天。他干脆蹲在人群旁边5米的石阶上,靠着连队发的对讲机打发时间。赵峰当时同时拿着两个手机,在两个平台上抢票,一个是滴滴,一个是出租车联盟,绑定滴滴的手机屏幕是亮着的,但是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滴滴基本不派出租车,它有自己的快车。」
他今年55岁,家住丰台。上次停在西城后,他一踩油门,直奔百度,“就盼着在这里接一单”。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5月初,北京春寒料峭,一阵北风让他踉跄了一下。“估计空今晚会坐车回去。”
在Xi的二七,老司机并不少见。看到互联网公司的交替,他们甚至觉得大厂员工面临的问题和自己没什么区别。哪里都不要老。陈大强开了一辈子出租车,也在首汽公司工作了一辈子。直到2015年,首汽转型为网约车共享平台,他自然从出租车司机转型为网约车共享司机。他曾经在百度里捡过一个看《有点权力》的人。他三十多岁,管着十几个人。最终,他也没有逃过裁员。他的孩子还在上学,背负着房贷,他也不知道自己下一份工作会何去何从,暂时只能找一份糊口的工作。“公司都一样,都喜欢年轻人。”陈大强说。
恐惧是真实的。去年年初,陆斌在楼下接了一群下班晚回家的人。下半年,他几乎没有收到猿类心理咨询的单子。反而上课了,楼下变得热闹起来。高楼倒下来的速度太快,吕斌害怕,但是没有司机愿意承认自己老了。第一辆车能开到60岁,陆斌7年,陈大强3年。出租车能开到65岁,赵峰还有10年。
如今,西二旗已经成为少数几个有固定名单的地方。“这么多公司,有些东西可能会从你的手指缝里漏出来。”一天后,我在西二旗同时遇到了赵锋和陈大强。陈大强接到了回昌平的工作,“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虽然赵锋仍在原地等待,但他找不到犀牛。牛椋鸟飞来飞去,他不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