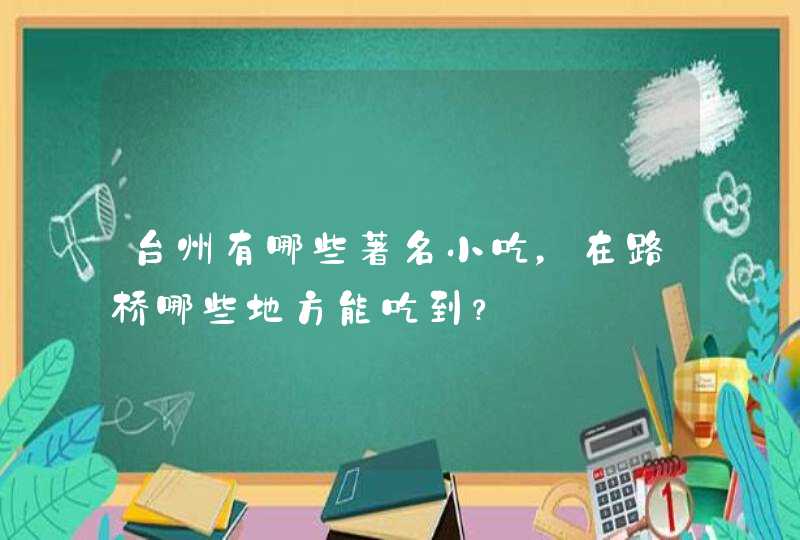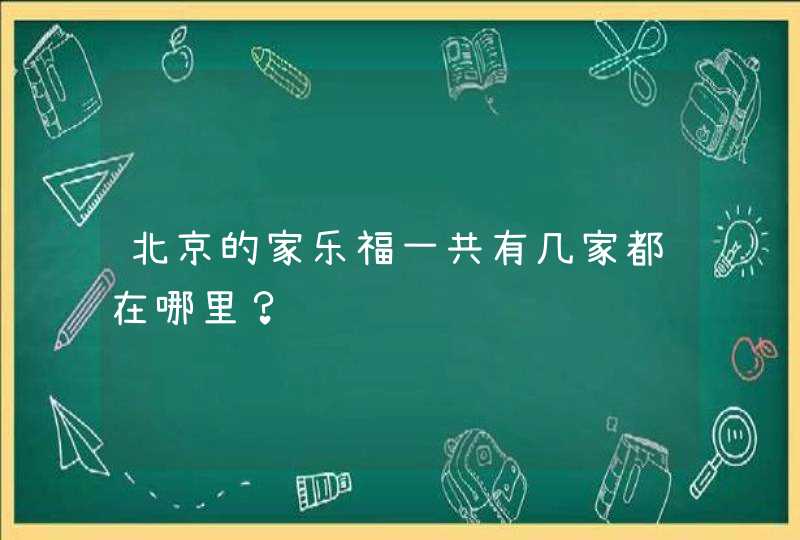——《阴天》莫文蔚
当你担心感情有问题时,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会遵循 “墨菲定律” (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假如你任其自由发展,结果必然是遗憾分手。
在这,我们总结了 感情发生危机的五大征兆 。
牢记这五点,当你在遇到的时候,一切都还来得及!
1
毫无缘由的减少和你的联系时间
喜欢一个人就是:
听到有趣的事情就想要立马讲给他听,看到路边的花就会拍照给他看,在商场见到他喜欢东西就会要买给他。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感觉无趣。
可是突然有一天变了,她变得不会再跟你讲,刚才又吃了什么,不会每天问你几点下班,不会再每天跟你讲早中晚安!
在你一通滔滔不绝之后,他只是以“嗯”、“哦”作为回复。
这种情况出现在异地恋居多。
都说异地恋就是跟手机谈恋爱:
你说感冒了要多喝热水,却又不能递到她手上;
你说想她,却不能立马出现在她楼下。
异地恋是辛酸的。
女生都是感性,看到身边的人出双入对,会让她更觉得一个人恋爱真的很累。
如果你还想挽救这份感情,放下所有的事情。
跨越山河大海也要立马出现在她面前,一个拥抱能融化所有的心灰意冷。
2
长时间相处,却从没规划你们的未来
首先,你需要确定一点,她是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还是有想法没有说出来。
这个其实很好判断,比如你可以跟他讲一下你的一些规划,再根据她对这些的反应来判断。
如果她对于你的提议或者说假设她提出了异议,那说明其实她心里是有谱的;
至少她对自己的方向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只是没有明确说出来而已,那这一类情况你不必太过在意;
如果对你说的这些他是一种无所谓、都可以、随便试试的态度,那么你需要警惕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我规划着我们的未来,你却想着离开)
你要重新审视你们是否真的合适。
如果一个对未来充满规划的你遇到的是一个更倾向于得过且过的她,那么未来肯定是困难矛盾重重的。
如果她总是不愿意正面和你交流关于未来的打算,就确实有在逃避的可能,那么也就很可能契合不了你对未来的规划。
当初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好感、新鲜感,被她身上的一些特质吸引,但是相处久了双方都有缺点暴露出来。
也许出于已经在一起时间很长分手可惜,可以互相迁就一下的这种想法,还是继续在一起,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涉及到未来的问题上,还是 继续迁就的话,也是没有好的结尾的。
因为最后维系两人一直走下去的,不会是他当初吸引你的带给你好感的各种特质,而是你们在未来生活上共同努力的心,这才是所谓的 稳定的前提 。
否则,长痛不如短痛。
3
突然的情绪低落以及不愿意沟通
人不可能整天情绪高昂的,总有低落的时候。尤其是在女生身上,情绪捉摸不定。
短暂的情绪低落是正常的,而且有可能遇到一些事情,总会导致我们情绪低落。
如果她不愿意和你沟通,也许是出于不想把这种情绪传染给你。这时候你就要跟 主动和她沟通去了解,带领她摆脱现状。
这样会进一步加深两个人的感情。另一种或许是出于双方之间的信任不够。
最近有一个学员面临分手问题。
他和现在的女朋友在一起已经三年了,也已经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最近却在这个节骨眼上 闹分手 。
由于调配的缘故,女生去年去了邻省工作,最近经常被领导留下加班。
通常会很晚才回家,打电话也不会说太多,几句日常之后就要休息睡觉了,他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安。
女友跟他解释过,由于最近公司要考核业绩,如果这几个月做出些成绩来,接下来一定能升职加薪,但是他心里总有点放心不下。
开始做一些疯狂的事,悄悄跑到女朋友公司楼下“蹲点”,趁着女朋友不在,偷偷翻看她的手机,打开手机位置共享等等,那么多“虚伪”的事儿他都做过。
后来意外被他女朋友发现了,双方不免会争吵一番,现在正临分手的窘境。
双方相处一定要给足对方信任,相互的理解,信任能更好地为沟通奠定基础。
4
对方开始对原来的目标产生动摇
当对方对原有目标开始动摇,并且有了新的规划的时候,你的异地恋可能要宣告结束了!
你们听说色达的红房子快要拆了,讲好一定要在这之前去过一次。
她也说想和你一起去巴黎,漫步塞纳河畔穿过巴黎圣母院,再来到浪漫的埃菲尔铁塔下接受你的求婚。
如今在提起,她只说: “巴黎圣母院已经倒了……”
在你提及你们共同定下的目标时,她总是有意识的一笔带过,或者明确表达了意愿。
5
不想频繁见面,有逃避心理
这个阶段,你会觉得你们之间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她总是在加班工作、学习,或是陪刚分手的闺蜜。
总之,找着一切你不得不接受的理由来搪塞。
这种关系很 敏感 ,千万不能持着“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 的心态,任由事态发展。
她可能还是因为和关系走到这一步太迅速,内心对于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有点恐惧,还需要时间去接受。
在这个时期不要给她太大的压力,表现出对她的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更展现出你的魅力。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她真的想离开你,你将要面对的是分手危机!
每段感情都有一个美好的开始,亦希望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在发现这些征兆出现时,一定要及时的处理。
谨记!沟通最重要。
PS : 看到过一个有趣的问答,一位女博主自称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一个细节,牵手两个人一起逛街牵手,十指相扣,松的那个人必定在日后提分手。
女博主当初和发小初恋在一起,两个人逛街,她紧紧拽着他,但是他松着手,连敷衍都懒得演,最终两个人分开了。
后来遇到一个喜欢她的男生,他和女博主手牵手,他拽特别紧,女博主却松着手。
最终她跟男生说我们以后还是不要有联系好了。
后来问了寝室的其他姑娘发现都是这样的,好奇心重的小伙伴可以去检验下,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
第七章一来二去的,我就在山庄里混熟了。其他人咱不说,我只给你说湖里的鱼。我是几乎每天吃完饭了,都要多领一个蒸馍。回来了到湖边,掰一疙瘩,在手里捻成馍花,朝湖里洒。有时候远处的鱼不过来,我就立起来洒,胳膊往高得扬。我心里想的是,不偏谁,不向谁,不管它们咋想。鱼是不知道饥饱的,哗啦啦水声一响,大的小的长得短的都游过来,你争我抢地往嘴里吞。现在,我只要到湖边蹴下来,水色就深一片,它们扑过来头仰着能立到水里。我看着它们吃干净了,心满意足地起身要走的时候,才觉得腿都麻了。静静站一会,环顾山庄一周,竟发现山庄的东西南北,除了假山里的公共卫生间,都有了我的阵地。上午我去总统房里喝杯西湖龙井,下午我到服务社里吃个奶油雪糕。白天我在湖西楼里面揽镜自怜,晚上我在月亮湾旁边思考人生。办公室里也经常会来人,事后听王爱云说有当司机的,有后勤的,大多是男人,都老老的,额颅上差不多有了不深不浅的抬头纹。他们进来,常常是与吴雅婷厮跟着,手脚不闲得戳戳打打。这时候我就要出去,我耳朵里听不进去叽叽喳喳的声音。
人一多,我其实能记清的,也没有几个了。但那个当着我的面跟吴雅婷打闹得不可开交的男人,我还是有些印象。不要脸的人,你碰见了,也一样印象深。这个人跟我实际上没什么瓜葛,但一直和吴雅婷不清不白。跟吴雅婷不清不白的男人好像还不少,多余我的就不说了,这男人权当是把那些代替了吧。男人姓刘,以前也是个经理,说是有一回警察扫黄,把他扫进去了,毁了名声,也就妻离子散。单位念及旧情,却不便再给个一官半职,自然成了闲人。四十都出头了,还是条光棍。人有些黑瘦,谢了顶,再时常掐个兰花指,用屁股上钥匙串里的指甲刀修指甲,说话轻声细语得,就有些娘娘腔。王爱云敢跟他开玩笑,经常“刘姐”“刘姐”地叫他。但我可从来没那样叫过。
水壶的肚子再大,壶嘴也就指头粗细,总要一股一股地往出倒,咱还是接着说我吧。第一个月的工资领了以后,我等不及晚上下班,中午到食堂吃饭,两口刨完,立即去买手机。但到了店里,却为了手机的便宜贵贱踌躇了。老板等得不耐烦,说:你要呀不?我眼睛不离柜台,说:要当然是要哩,看要哪一个呀。他说:哎呀,多少就差个百十块钱。我把他看了一眼,心想你说得轻巧,百十块钱挣来容易的?但还是狠心掏钱,手一抖钱却掉在地上,捡起来如数给了人家,出了门心就跳得“嗵嗵”地。往回走的路上,总觉得后头有人跟着,也觉得兜里沉甸甸地像装了块石头。知道东西贵重,一路上手插到兜里紧紧把手机攥住。进了单位,坐到湖西楼了,才把手机掏出来仔细端详了一阵。当天晚上寻了个没有人的黑处,把电话打到对门的家里,问候了,母亲被叫过来,我听见话筒里有了“沙沙”的声音,知道她接起来了,急忙说:喂,妈。她说:是皓子呀。这么晚了,有啥事啊打搅人家。我问过她和祖父的身体和近况,便说自己买了手机,让她把号码记住,以后好联系。她说:才挣了那么点钱就买手机呀?今年菜价恁便宜的,好些人觉得不够跑路和辛苦钱,直接拿锹铲到地里当肥料上了,你花钱手恁大的?我就说是工作需要,要相互联系的话,她也就罢了。我又让她给家里也装个电话,省得半夜了到人家家里。她说:咱一天也没有啥业务,座机费又贵,把那钱省下干啥不行?我说:你要是没有钱了,我给你寄上些。她说:不用,不用,你把钱攒到手里就行了。家里啥都不缺,我跟你爷都好,没有事就早早挂了,电话费也要钱哩。我明白她的意思,叮嘱了她平日注意安全,手里活忙了吃饭也不能将就,炒菜要多倒些油,天黑了就往回走,关上门了要再找个杠子顶住之类的话,也就把电话挂了。
心里头酸了一阵,但日子还是要过。谁知道时间不长,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这秘密,我只要一想起来,就心惊肉跳。
我值班的一个晚上,烫了一杯茶,正轻轻地往嘴里抿,手机铃声响了。我吓了一跳,胳膊一抖,煎水就把嘴唇给烫了。我不是胆小,我是还没有适应有手机的日子。嘴里的水喷出来,下意识两腿往开一张,一滩水流到了地上。我心里起了一道火,连来电显示看都没看,接了电话,声音躁躁地,说:谁呀!那头是玉梅的声音,尖尖地说:你个死皓子,连我电话都不存啊!我说:哥看是你的号码,才没有骂人,我给你说!她说:咋了嘛,谁把你咋了?我不怕玉梅笑话,说:正喝茶哩,电话一响,把嘴烧了。她嘻嘻笑了一阵,说:大半晚上的,你还喝茶,不怕睡不着啊。我说:少废话,啥事,说!她把声音压低了,神神秘秘地说:有一场好戏哩,皓子你看不看?我身子往前倾了一下,说:啥好戏?她说:你去到二区三院转转,去了你就知道了。把电话挂了。
“月黑风高杀人夜”这话你听过吧?我其实也有些匪夷所思,为啥许多千奇百怪的事,都是发生在晚上。是因为它静悄悄地,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想得多了,又容易走火入魔,把脑子想的事情干出来吗?但咱现在不说杀人的事,你不要紧张。我出了湖西楼,迎面一阵凉风,我心里说都马上五月了,温差还这么大。一边走一边扣西服纽子。蛐蛐还是蚂蚱在草丛里“吱吱”地叫唤,像老鼠一样,只不过声音扯得能长些。而湖里却有了蛤蟆还是青蛙,“呱呱”地一声高过一声。湖水经月光一照,变成了一面黑黑的镜子,桃树柳树和假山都在镜子里游动。房檐上挂着的灯笼放着红色的光,把冬青树映得红不红绿不绿地不是个颜色。影影绰绰,隐隐约约,朦朦胧胧,星星点点的光,从湖水里反射到墙壁上,湖面一动,光点就一动,像是有许多人在太阳底下拿了个镜子碎片在反射阳光一样。黑暗里,路灯把我的影子拉长,影子一会走到了我前面,一会又落到了我后面,我不由得就有些紧张。
到了院子门口,我屏住呼吸,侧耳贴着门缝听里面的动静。里面跟外面一样,还是蛐蛐的叫声。轻轻把门推了推,没有推动,知道是门闩卡住了。想起来每个院子都有个小门相连,至于这个小门是为了串门方便还是其他用途,谁说得清楚呢。不管它,方便我就行了。到了二号院子,休息室里灯亮着,知道是晚上值班的服务员,脚步轻轻地走过去。才过了小门,就听见一阵浪笑,像荡妇被挠了胳肢窝。这笑声听得我心痒痒,快步走到亮灯的厢房跟前,猫到了窗户底下,姿势还没有摆好,又听见女人的声音,说:你干啥嘛!讨厌死了。我一惊,明明是吴雅婷的声音。我既兴奋又紧张,迫不及待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两手勾住了窗台,把屁股撅起来,眼睛放到了窗台上。
窗帘竟然没有拉,透过哑光白的窗户贴纸,我隐约看到一位光头的中年男人和褪去外套的吴雅婷。男人伸出胳膊搂住吴雅婷的脖子,说:想死我了,宝贝蛋子。来,让我亲一下。说着就把嘴往过送。吴雅婷把嘴推出去,娇滴滴酸溜溜地说:去,你个老流氓。你答应给人家买的衣服呢?男人恍然大悟,消失在窗户里,旋即又回来,手里多了件东西,我睁大眼睛,想看清是什么东西让男人像日本人的汉奸一样笑出淫荡的声来。但我马上听到吴雅婷说:呀!讨厌,谁让你给人家买内衣了。我一听是内衣,脸上烧了一下,却眼睛睁得更大了。吴雅婷接过内衣,看了看,说:怎么是粉红色呀?男人说:粉红色好看,骚!吴雅婷说:你滚。好看也不能随便给你看!接着又问到:就这么两件吗?男的说:哎呀,这两天打牌输了,屋里那母老虎把钱看得又紧。然后用迫不及待有些颤抖的声音说:快快快,穿上,穿上试试。说着就上去脱吴雅婷的衣服。吴雅婷娇嗔道:你讨厌,转过去,我自己来。男人哈哈地笑,说:你事多的很,赶紧,赶紧。吴雅婷说:你不转我转。说着就转了过去。
吴雅婷的胳膊像带鱼一样从袖子抽出来,窗户里就有了她白白的脊背。她的手背过来,去解内衣的扣子,模模糊糊地看起来像倒立着的两条弓着脖子的眼镜蛇在亲嘴。嘴巴一动,扣子便开了。松紧一动,我心里颤了一下,觉得身上有个东西热起来。男人的头也随之一动,像咽了一口唾沫。他右臂弯曲着,像挖掘机的爪子,一把从吴雅婷的两腿间穿过去,左臂顺势勾住吴雅婷倒下来的脖子。吴雅婷“啊”地惊声尖叫,说:你个色狼,坏蛋,放我下来!吴雅婷转过来的脸对向了窗户,我急忙蹲了下去。听见男人说:今天非把你办了不可!“嗵”地一声,听着像是吴雅婷被扔到了床上。我靠着墙,大口地喘气,下意识地往左右看了看,院子门还是关着,上房门也还是闭着,害怕小门有人过来,头低着像鸭子一样走过去,扶着墙探出去一只眼,看清了门缝还是那么宽,还是我进门的时候用手固定住的角度。这时候房子里有了哼哼唧唧的声音,像是被人叫起床时胡乱应付的声音。我头皮麻了一下,觉得裤裆里有些顶,知道蹴着往过走不方便了,再说也不是啥好事情,就准备走。但房子里却又传来“啊”地一声,立时我身上就像通了电,猛得抖了一下,眼睛一闭,脑海里出现了许多景象,有公鸡压蛋,母猪配种,野猫发情,还有狗叠罗汉,驴马翘鞭。吴雅婷似真似假,如梦如幻的哀鸣,像水一样无孔不入,漫到了整个院子里,钻进我的耳朵,渗进我的毛孔,我全身都痉挛了。
第二天清晨的早会上,我在上面讲话,玉梅在下面捂着嘴偷偷地笑,我拿眼睛剜她,她还是笑。开完会我径直朝她院子走。她在前面走着,听见了后面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我用手狠狠把她指了一下,她又是一笑,在前面跑开了。
玉梅开了门就往休息室跑,她害怕我收拾她,但我没有收拾她,而是躺到了床上,脚搭在床尾的架子上抽烟。我是乏了,晚上没有睡好。玉梅先把烟灰缸拿来,放在我手底下的桌子上,又沏了杯茶给我递,我下巴把桌子一指,她把杯子往桌上一墩,说:你咋比我老汉还势大,我成你的丫鬟啦?我说:困的。烟抽了两口,嘴里苦,就把烟在烟灰缸里捻灭了。她就笑了,说:咋?昨晚上看了一夜啊?眼睛把瘾过了?我也笑了笑,说:呀,我才发现,你比我还流氓啊。她还是笑,说:你早上没检查一下床板,看有窟窿没?我猛得变脸,一个仰卧起坐直起腰来,一巴掌扇到她脸跟前。她却不惧我,把我伸到我面前,说:给给给。我在她脸上摸了一下,她踢了我一脚。
嘻哈了一阵,玉梅嫌房子呛,过去把门开了,说:我看你最近跟童曼瑶走的还近,咋,准备处对象啊?我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处对象我也是跟你处啊。玉梅说:滚一边去,一天到晚没有个正经,姐是有夫之妇了。我说:有夫之妇才有竞争力嘛!玉梅说:去去去,我才不是那样的人。我才要反驳,她却凑到我跟前,正色说道:耗子,我跟你说啊,单位里面的人,你最好还是不要沾,这是前车之鉴。我看了她一眼,她眼神怪怪的,我没有理她,端起杯子喝一口茶,做出努嘴要喷她的样子,咽了茶说道:这话是啥意思?她说: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反正我这样觉得。我眼睛睁大了,说:那你是车还是鉴?玉梅楞了一下,说:我?头低了低,又说:我是没办法。这我就听不懂了,说:什么没办法,我就不相信,他雷大头还能霸王硬上弓不成?玉梅叹了一口气,说:唉,实际上男人跟女人也就那么点事,看开了,想通了,啥都好办。她这话说得没盐没醋得,我听着没劲,感觉困了,说:不跟你说了,我睡觉呀,有事叫我。玉梅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欸,耗子,说睡觉呢,你在外边租的房子吗?咋没有在宿舍见过你?我闭着眼睛,说:我跟你老汉雷大头在一块睡着哩。她急促地说道:你也在红房子住着?我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她又追问:你一个人?我又嗯了一声,快睡着了。她过来摇我的胳膊,说:起来起来!我睁开眼睛,不耐烦,说:咋啦咋啦!她睁大的眼睛,像两个核桃,说:你咋也睡到红房子去了?我应付着:领导安排的嘛!她突然说:那里面死过人!
我一骨碌就爬了起来。
这就要说起我不愿提起的那件往事了。这件事,我虽然没有经过,但我只要进了红房子的大铁门,玉梅口述的那件事情,却仿佛我就飘在红房子整个区域的上空,清清楚楚地目睹耳闻了一样。人有的时候为了逃避责任,常常要把有些事情用迷信来解释。但我不,我承认我只是紧张过,害怕过,也恐惧过,其余的,都是老天安排好了的,跟谁跟啥都没有关系。如果非得要总结,还是那句老话,谁年轻的时候没干过几件瞎事情呢?
玉梅端起我的水喝了一口,眼光高高地发散了出去,仿佛想要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要开口了,却扭头看了门外头,起身把门关了,坐下来,叹一口气,说 唉,这都有三年了吧。时间过得真叫个快。那时候我刚进山庄五个多月,因为表现好就被调到红房子当服务员。谁能想到事情就出到我手里呢?以前的餐饮部有个叫李风的,是主管。小伙子白白净净的,个子又高,人也机灵,每次见了我都梅姐梅姐地叫。后来跟他们餐饮部的一个叫王灿的门迎好上了。两个人黏黏糊糊地成天出双入对,走到哪人都羡慕着,说是咋就恁般配的,号称是当时两个人都快谈婚论嫁了,我们都等着喝喜酒,吃喜糖呢,却出了人命。
这个事啊,就应了咱们陕西的一句话:蔫蔫骡子踢死人。玉梅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又重重地出了,再喝了一口水,顺手用袖子把嘴抹了,一幅不愿回忆往事的样子,接着说:那天晚上也是怪,我吃了下午饭回去才坐下,就有客人过来退房,退就退吧,客人来了走了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我给前台打电话说退房的事,话筒还没有放,就又有客人把房卡给我往过递。前前后后,都跟商量好的一样,五拨客人退了房。我又是清点物品,又是打扫卫生,累得兮兮的了,坐下来歇,眼睛就开始跳,先是左边,这个跳还跟平常那个不一样,是感觉好像有人轻轻地揪你的眼皮子,一揪一松那种感觉。我就赶紧在心里想,到底是左眼跳灾呢还是右眼跳灾?心里一急,硬是想不起来,感觉咋样念起来都顺口。后来却两只眼都跳,一时慢了,一时快了,但就是跳不到一个点子上。我使劲把眼镜挤了好几下,不管用,我就把眼镜闭上,闭上了用大拇指和食指一个指头压一个。压着是不跳了,但一放马上又开始跳。我心里有些害怕,走到卫生间去用凉水洗了把脸,洗过了连镜子也没敢照,又回来坐下,但眼睛还是跳着,我就自己哄自己说这是累的吧,都退了也好,我晚上值班没有人打搅,偷着睡个好觉。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正好是十点。
玉梅眼睛看向我,问道:你知道我为啥记得这么清?我没有说话,看着她,她头上似乎渗了汗,晶莹莹地被灯映出来些白光。我扯了些卫生纸给她擦了一下,她手上来接住,自己擦起来,擦过了揉成一疙瘩捏在手里,说:就是因为这时候有两个人进来了,这两个人,正是李风和王灿。我心里还说这两个谈情说爱哩,跑到我这儿干啥来了?李风就走过来,笑着说:梅姐,帮我开个房吧。我看娃一脸正经,不像是要胡搞,又看了一眼王灿,那姑娘人家也没有害羞,笑了一下。我当时就想人家是不是双方父母要见面了,这边的房子看起来毕竟能体面些。想着他俩也挣不了多钱,也就没有给前台说,就给把房子开了。再叮咛了时间不要太长的话,都要走了,李风却把我胳膊拉住,硬是给我塞了一把糖。
玉梅歇了一口气,接着说:我重新坐下来,嘴里吃了糖,甜甜的也把眼睛跳的事情给忘了。过了看有半个多钟头吧,我都快瞌睡了,一个餐饮部的服务员进了门,胳膊擎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有个老碗。按规矩一般服务员过来送餐我是不过问的,只看一眼他们的工装。但那个服务员走路怪怪的,腰挺得直,下脚却轻,步子换得也慢。我随口就问:欸,干啥的?服务员连我看都没看,脸上没有表情,冷冷地说:送——餐。声音压得低,拖得也长,直接往二楼去了。唉,我真是个猪脑子,我应该能想到不对劲的。但我那阵真的是困了,皓子,你相信我不?
我轻轻笑了一下,把头点了点,玉梅咽了一口唾沫,头向前伸了一下,接着说: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服务员,叫张平波,而他的餐盘底下,藏了一把从厨房偷来的菜刀。我那时候是真正瞌睡了,正迷迷糊糊着,猛然间听到了一声毛骨悚然的尖叫。我一下惊醒来,以为是在做梦,但马上尖叫又传来了,比刚才那一声更尖,更让人害怕。你不要嫌我说话难听,我也不是对过去的人不尊敬,但那声音听起来真的跟杀猪一模一样。我头皮一下子麻了,身上的鸡皮疙瘩起得能把衣服撑起来。立马就往上跑,但才迈了一步,腿就软得瘫到了地上,扶住楼梯栏杆爬起来,想着顺手抓个东西防身,但没有,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劲,抓住那木头栏杆,猛得一拽,“咔嚓”一声,手里就有了东西。
说到这儿,玉梅停了一下,看着我问:你是不是以为我胆子还挺大的呀?我听她的语气知道她要转折了,也没有笑,只是把她看着,她接着说:等我跑上去,看见张平波那张脸,我一点都不给你夸张,我也杀猪似的叫了一声,手捂了眼睛,直接从二楼滚到了一楼。我这辈子再也不愿意看见那样的脸。那不是人,是一个妖魔鬼怪在那站着,他满身满脸都是血,黑工服已经染成了紫色。最害怕的是他的眼睛,好像就没有眼珠,只有眼白,睁得大过了核桃。但明明是白的,却又感觉额颅上的血流进去了,发着红光。而他手里提的那把菜刀,刀尖上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血。
玉梅似乎不愿再回忆下去,她两只手上来盖住了脸,粗重的呼吸从指缝里传出来,胳膊明显有些抖。我不知该怎样打破沉默,等了半天,问道:那后来呢?她两手放下来,指头上明晃晃地有了水,我知道那是眼泪。她眼睛快速地眨了几下,清了清嗓子,说:后来不用说你也能想来了吧?保安到了以后喊叫让张平波把刀放下,但他没有任何反应,其他人也就都不敢近身,听说是僵持了有十分钟吧,有人绕到后面把他扑倒了。倒的时候,身子是直直地倒下去,硬得像窑里烧出来的人。李风当场就没有了呼吸,王灿精神失常了。你相信吗,李风最后连眼睛都没有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