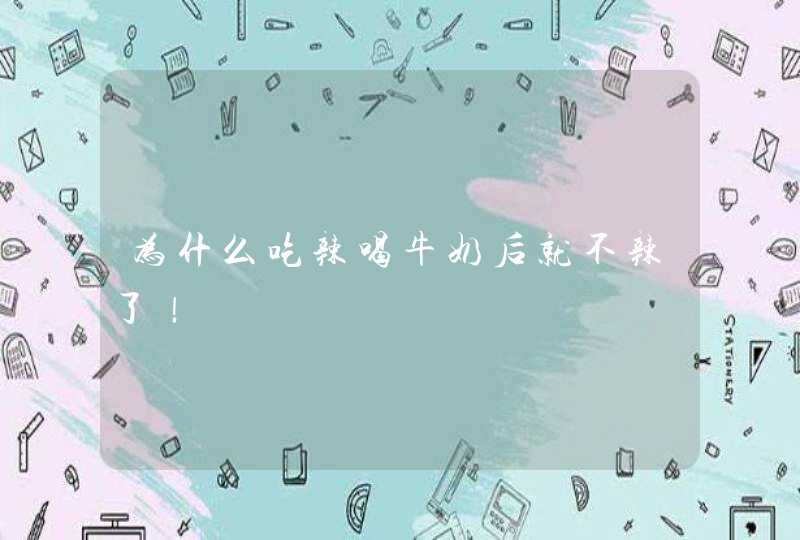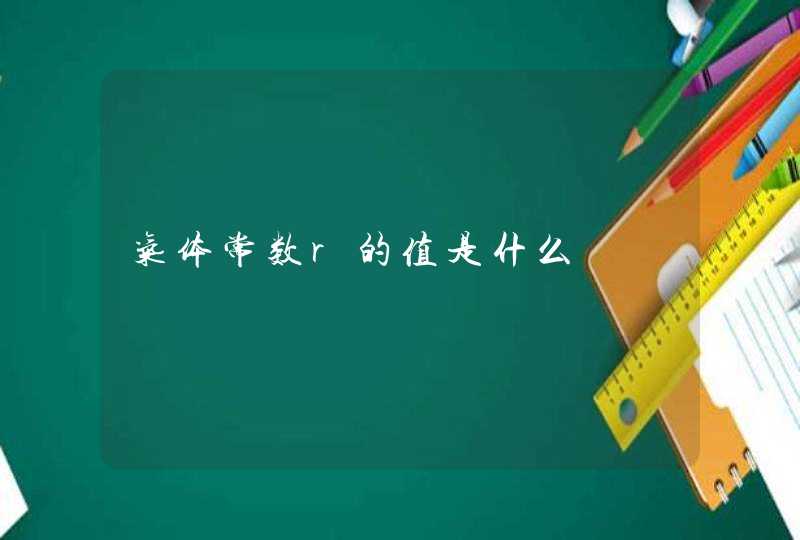“与人为徒”、“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的概念出现在庄子《人间世》一篇中颜回出仕卫国前与孔子的对话中。《人间世》讨论的中心是庄子的处世之道。全篇假托三个故事:颜回出仕卫国前与孔子的对话,叶公子高将出使齐国时向孔子的求教,以及颜阖被请去做卫太子师傅时向蘧伯玉的讨教。以此说明处世之难,不可不慎,而怎样才能应付艰难的世事呢?《庄子》首先提出要“心斋”即“”虚以待物”,再则“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第三,要“正女身“、”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颜回处仕卫国前与孔子对话,给出的便是“心斋”这一智慧锦囊。在这则寓言故事中,卫国国君年轻识浅,独断专行,鱼肉百姓。颜回想用孔子的仁政理念去卫国改变卫国国君,就来与孔子告别。孔子一听颜回想要带着改变卫国的心态去卫国,认为颜回此次深入险境,必将凶多吉少。卫国当前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境况,根源在于卫国国君的身上,他本来就是独断专行,听不进谏言,鱼肉百姓之徒。他如果是能欣赏贤臣、能听得进谏言之人,就不会出现当前国内的状况,他的身边不乏良臣能将,你这时强行去推行仁义,带着改变卫国国君的心态去卫国,在强烈的功利心之下,你越是想要这个结果,你越是无法保有云淡风清、心平气和的心境,你推行的仁义国君本来就难以听得进去,而你的心性一乱,势必会与国君产生分歧、冲突,最后引来灾祸,前有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的历史事件为鉴。于是孔子进一步问颜回,你如果一定要去,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颜子以“以人为徒”、“以天为徒”、“以古为徒”阐述了他的应对策略。
第一,与天为徒,内心诚直,固守原则。内心诚直的人,就是与自然为同类,天人合一,知道自己跟国君本质上都是属于天生的,在自然属性上是同类的,在这个层面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又何必希望自己的言论得到别人的赞同,或者是介意别人的不赞同呢?有着这样心态的人就像孩童一样,保有赤子之心,就是与天为徒者。
第二,与人为徒,外表恭敬、顺应现实。表面屈从的人,认同于社会,和世人一样。譬如手拿朝笏躬身下拜,这是人臣应尽的礼节,人家都这么去做,我敢不这么做吗?一个人,做大家都在做的,谁也挑不出他的纰漏来,他便能被社会所认同。
第三,与古为徒,内心自有主见,上比古人。上比古代贤人,跟古人为同类,他们的言论虽然很有教益,指责世事才是真情实意。自古就有这样的做法,并不是我自己的编造,这样做,虽然正直不阿却也不会受到伤害,这就叫做与古人为伍。
总的来说,颜子的应对策略是保持内心诚直,相信自己与国君本质相同,只要自己内心固守原则,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说自己该说的话,最终能够感化国君,不必在意于自己的言行一时得不到认可。因此,与天为徒者,更像是拥有信仰的一群人,《道德经》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同的人归其本质都来源于那个“一”,只要自己与天为徒,亲近自然,恪守自然之道,就能保有赤子之心,获得行事的力量源泉与信念支撑。“与人为徒”则是在现实中通过行为上融入环境,表现得合群,让别人找不出自己的矛盾,获得别人的认可,从而周全自己。“与古为徒”则从浩瀚的历史典故中,汲取智慧,助力自己达到目的。
在孔子的启发下,颜子想出了他自己觉得既能周全自己,又能帮助自己去卫国推行仁义,教化国君的策略。但孔子仍然对他的策略提出了批评,认为颜回仍然带着“师心成见”,很难获得成功,因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纠正,就是有所效法也会出现不当,你又怎么能祈求能够教化国君呢,还是太固守于自己的成见了。于是进一步引出“心斋”即“虚以待物”的处世哲学。
“以人为徒”、“以天为徒”、“以古为徒”的策略都还存有缺陷,颜回一心想要去卫国推行仁义、教化国君的目的心太重。“心斋”要求的是“虚以待物”,需要的是清空自己的内心,以心做道场,去体悟自然之道,抛弃私心杂念,名利之心,“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以一种通透圆融之心,能够看清形势,条件允许的时候则奋力一搏,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则保全自己,一宅而寓于不得已,以心做道场,修炼心性,积蓄力量。
通过“心斋”修炼一颗通透圆融的心,虚以待物获得应变的灵活性,去更清晰的看清外部环境,体悟自然之道,而这也是“与天为徒”的一个前提,你只有更好的体悟自然之道,才能更好的保有赤子之心,获得在人世间更强大的精神支撑与力量之源。“与人为徒”则是一宅而寓于不得已的一种行世的方式,现实的环境与自己的理想世界不同,那么就先去做到表面上的合群,保全自己,积蓄改变的势能,而在心性上不被环境所改变。“与古为徒”,从历史的经验中充实自己应对人世困难的宝具库,从历史中获得解决各类问题锦囊妙计。
原文:
三曰:
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
注释:
○去尤:就是去掉赘尤。尤:通囿。蒙蔽、局限之义。
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颜色,窃鈇也;言语,窃鈇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尢也。
注释:
○鈇(fu 夫):通斧。
○意:疑。
○无为:没有
○谷:坑。
邾之故法,为甲裳以帛。公息忌谓邾君曰:“不若以组。凡甲之所以为固者,以满窍也。今窍满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组则不然,窍满则尽任力矣。”邾君以为然,曰: “将何所以得组也?”公息忌对曰:“上用之则民为之矣。”邾君曰:“善。” 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知说之行也,因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之者曰: “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组者,其家多为组也。”邾君不说,於是复下令,令官为甲无以组。此邾君之有所尢也。为甲以组而便,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也?以组不便,公息忌虽无为组,亦何益也?为组与不为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用组之心,不可不察也。
注释:
○邾:古国名。故址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为甲裳以帛:做战衣常用帛。裳:同常。
○公息忌:人名,旧作公息忘。
○组:绶带。
○满窍:孔窍全都塞满。
○任力:承受力。
○伤:毁败。
○累:牵累。
鲁有恶者,其父出而见商咄,反而告其邻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恶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恶,尢乎爱也。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然後能知美恶矣。《庄子》曰:“以瓦殶者翔,以钩殶者战,以黄金殶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鲁人可谓外有重矣。解在乎齐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则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独,必不合於俗,则何可扩矣。
注释:
○恶:丑陋。
○商咄:人名。据说长得很美。
○反:同“返”。
○庄子曰:引文见《庄子·达生》。文字略有出入。
译文:
世上凭着听闻下结论的人,往往有所局限。往往有所局限,那么凭听闻下的结论必定是谬误的了。受局限的原因很多,其关键必定在于人的有所喜爱和有所憎恶。面向东望的人,看不见西面的墙,朝南看的人,望不见北方。这是因为心意专于一方啊。
有一个丢了斧子的人,猜疑是他邻居的儿子偷的。看他走路的样子,象偷斧子的。看他的眼色,象偷斧子的,听他说话,象偷斧子的;看他的举止神志,没有一样不象偷斧子的。这个人挖坑的时候,找到了他的斧子。过了几天,又看见他邻居的儿子,举止神态,没有一样象愉了斧子的。他邻居的儿于没有改变,他自己却改变了,他改变的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原来有所局限。
邾国的旧法,制作甲裳用帛来连缀。公息忌对邾君说:“不如用丝绳来连缀。大凡甲之所以牢固,是因为甲连缀的缝隙都塞满了。现在甲连缀的缝隙虽然塞满了,可是只能承受应该承受的力的一半。然而用丝绳来连缀就不是这样。只要连缀的缝隙塞满了,就能承受全部应该承受的力了。”邾君以为他说得对,说:“将从哪里得到丝绳呢”公息忌回答说:“君主使用它,那么人民就会制造它了。”邾君说:“好!”于是下命令,命争有关官吏制作甲一定要用丝绳连缀。公息忌知道自己的主张得到实行了,于是就让他家里人都制造丝绳。有诋毁他的人说。“公息忌之所以想用丝绳,是因为他家制造了很多丝绳。”邾君听了很不高兴,于是又下述命令,命争有关官吏制甲不要用丝绳连缀。这是邾君有所局限!制甲用丝绳违缀如果有好处,公息忌即使大量制造丝绳,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用丝绳连缀没有好处,公息忌即使没有制造丝绳,又有什么益处呢公息忌制造丝绳或不制造丝绳,都不足以损害公息忌的主张。使用丝绳的本意,不可以不考察清楚啊。
鲁国有个丑陋的人,他的父亲出门看见商咄,回来以后告诉他的邻居说;“商咄不如我儿子。”然而他儿子是极丑陋的,商咄是极漂亮的,他却认为极漂亮的不如极丑陋的,这是被自己的偏爱所局限。所以,知道了漂亮可以被认为是丑陋,丑陋可以被认为是漂亮,然后就能知道什么是漂亮,什么是丑陋了。《庄子》说:“用纺锤作睹注的内心坦然,用衣带钧作赌注的心里发慌,用黄金作赌注的感到迷惑。他们的赌技是一样的,然而所以感到迷惑,必然是因为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就会对它亲近,因而内心就会不安详。”那个鲁国人可以说是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了。这道理体现在齐国人想得到金子,以及秦国的墨者互相嫉妒上,这些都是因为有所局限啊。老聃就懂得这个道理,他象直立的木头一样自行其事,这样必然与世俗不合,那么还能有什么能使他内心不安昵
庄子·内篇·人间世
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
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
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
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
白话译文
颜阖将被请去做卫国太子的师傅,他向卫国贤大夫蘧伯玉求教:“如今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德行生就凶残嗜杀。跟他朝夕与共如果不符合法度与规范,势必危害自己的国家;如果合乎法度和规范,那又会危害自身。他的智慧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却不了解别人为什么会出现过错。像这样的情况,我将怎么办呢?”
蘧伯玉说:“问得好啊!要警惕,要谨慎,首先要端正你自己!表面上不如顺从依就以示亲近,内心里不如顺其秉性暗暗疏导。即使这样,这两种态度仍有隐患。亲附他不要关系过密,疏导他不要心意太露。外表亲附到关系过密,会招致颠仆毁灭,招致崩溃失败。
内心顺性疏导显得太露,将被认为是为了名声,也会招致祸害。他如果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你也姑且跟他一样像个无知无识的孩子;他如果同你不分界线,那你也就跟他不分界线。他如果跟你无拘无束,那么你也姑且跟他一样无拘无束。慢慢地将他思想疏通引入正轨,便可进一步达到没有过错的地步。
你不了解那螳螂吗?奋起它的臂膀去阻挡滚动的车轮,不明白自己的力量全然不能胜任,还自以为才高智盛很有力量。警惕呀,谨慎呀!经常夸耀自己的才智而触犯了他,就危险了!你不了解那养虎的人吗?
他从不敢用活物去喂养老虎,因为他担心扑杀活物会激起老虎凶残的怒气;他也从不敢用整个的动物去喂养老虎,因为他担心撕裂动物也会诱发老虎凶残的怒气。
知道老虎饥饱的时刻,通晓老虎暴戾凶残的秉性。老虎与人不同类却向饲养人摇尾乞怜,原因就是养老虎的人能顺应老虎的性子,而那些遭到虐杀的人,是因为触犯了老虎的性情。
爱马的人,以精细的竹筐装马粪,用珍贵的蛤壳接马尿。刚巧一只牛虻叮在马身上,爱马之人出于爱惜随手拍击,没想到马儿受惊便咬断勒口、挣断辔头、弄坏胸络。意在爱马却失其所爱,能够不谨慎吗!
知道世事艰难,无可奈何却又能安于处境、顺应自然。此句出自庄子《人间世》。
原文节选:
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生!夫子其行可矣!
译文:
所以侍奉双亲的人,无论什么样的境遇都要使父母安适,这是孝心的最高表现;侍奉国君的人,无论办什么样的事都要让国君放心,这是尽忠的极点。注重自我修养的人,悲哀和欢乐都不容易使他受到影响,知道世事艰难,无可奈何却又能安于处境、顺应自然,这就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做臣子的原本就会有不得已的事情,遇事要能把握真情并忘掉自身,哪里还顾得上眷恋人生、厌恶死亡呢!你这样去做就可以了!
扩展资料
《庄子·人间世》简介
《人间世》是一篇《庄子》内篇中的文章。本书的中心是讨论处世之道,既表述了庄子所主张的处人与自处的人生态度,也揭示出庄子处世的哲学观点。
全文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至“可不惧邪”,以下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假托三个故事:孔子在颜回打算出仕卫国时对他的谈话,叶公子高将出使齐国时向孔子的求教,颜阖被请去做卫太子师傅时向蘧伯玉的讨教,以此来说明处世之难,不可不慎。
《庄子》首先提出要“心斋”,即“虚以待物”。再则提出要“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第三提出要“正女身”,并“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归结到一点仍旧是“无己”。
第二部分着力表达“无用”之为有用,用树木不成材却终享天年和支离疏形体不全却避除了许多灾祸来比喻说明,最后一句“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便是整个第二部分的结语。前后两部分是互补的,世事艰难推出了“无用”之用的观点,“无用”之用正是“虚以待物”的体现。
“无用”之用充满了辩证法,有用和无用是客观的,但也是相对的,而且在特定环境里还会出现转化。
《庄子》与《归藏》《黄帝四经》《老子》等著作共为中华民族的几部源头性经典,它们不仅是哲学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古代圣哲关于文学、美学、艺术、审美的智慧结晶。庄子等道家思想是历史上除了儒学外被定为官学与道举的学说。
《庄子》不仅是一本哲学名作,更是文学、审美学上的寓言杰作典范。更是对中国文学、审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深远影响。庄子寓言的出版和研究使得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精神得以发扬,在现实意义上,更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做出了不可忽视的精神铺垫。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间世 (中国哲学、文学作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庄子 (道家学派经典著作)
庄子说:“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是什么意思呢?
形,是外形,外表上。就,是靠近,接近。心,是内心。和,是祥和,平静。
那么连起来就是外表上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了,但内心却是不起波澜的,这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做人要外圆内方呢。
下面是庄子在《人间世》上说的一个小故事:
颜阖收到卫灵公的命令,要他去教太子读书,他内心感到忧愁,于是跑去问大圣贤蘧伯玉,颜阖说:“我们的这个太子啊,我看他天生就是个好杀之人。
如果我去当他的老师啊,混混日子还行,可这样的话就对不起这份薪水,对不起天下百姓了啊。但是,如果我用心去教他那些圣贤之道,必定会引起太子反感,我这个人头可又不保了啊。
太子这个人还是很聪明的,可是呢,他的聪明往往都放在了别人身上,他从来不知道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你看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啊?”
蘧伯玉说:“你说得太对了,但现在上天给了你这个使命,你就应该顺应天命去做啊。你可以时时保持警戒之心,做事说话都要小心谨慎,你要首先自己能行得正,坐得直啊。
你可以表面上和太子拉近距离,‘和其光,同其尘,’但是呢,你的心不能变。虽然这样做还是有一定危险的,但我相信你,你能够把握恰到好处的状态,不至于陷得太深。
比如说啊,太子喜欢打猎,你也就跟着陪他去打猎,但是呢,你应该知晓‘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的道理,一定不能真心地想去打猎,这是借机亲近太子,并能教给他一些东西,如果你的心陷进去了,那就危险了。
另外一方面呢,你也不可以太过于激进,不能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而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去进言,这样做,也是很危险的。
你应该跟随着太子的水平,去变化调整你教育他的方法,比如,太子是幼儿园水平,你就要是幼儿园老师,太子是高中水平,你就要是高中老师。
你要只领先他一点点,不要给他设置太高的目标,你要跟着他一起成长,这样还是有可能会达到最终目的的。
如果你按照以上说的这样来做,应该很难挑出毛病的,一方面能够达到既教育了太子的目的,另一方面又不至于伤害了自己的性命。”
庄子《人间世》:无迁令,无劝成
庄子《人间世》:祸从口出,动辄得咎
庄子《人间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庄子《人间世》:什么是“心斋”?
在《庄子》内篇中,以“孔子”为主角的寓言颇多,这些与孔子相关的论述,多集中于《人间世》、《德充符》以及《大宗师》等篇章。
内篇中的孔子,时而受到讥讽,时而论大道,看来形象并不一致。因此,庄子对孔子的态度究竟如何,一直是论者热衷探讨的问题。
庄子画像
是以,玲珑试图回归原点,逐步探求庄子如何塑造孔子形象,诠释孔子境界。在内篇中,以孔子为主角的预言首先现身于《人间世》。孔子寓言不出现于《逍遥游》、《齐物论》,而出现于《人间世》,想来也是饶富趣味的。这并非是说孔子不能逍遥,无法齐物,而是说孔子就像多数平凡人一样——身处人间世,必须面对人间的事。
安之若命,乘物游心
人间的事复杂难解,平凡人却无可逃避,庄子常常借用孔子之口,说明人事之复杂、处世之艰难。在《人间世》中,就记载着一则“叶公子高将使于齐”的事例。
叶公子高出使齐国之前的恐惧,很能说明人处于纷乱尘世的无奈。事如果不成,将有人道之患;事如果成了,则有阴阳之患。无论如何,似乎都避免不了祸患降临。这样的困境并非是自己招致的,只能说是时、命使然,但人们却必须时常面对它所带来的灾祸。
“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叶公子高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免除其患,可见在他心中,孔子正是善于处事的“有德者”,而这也正是孔子在此寓言中的角色定位。
《孔子》——孔子剧照
孔子的人生取向毕竟与“避世之士”不同,他认为“子之爱亲”、“臣之事君”皆是人无可逃避的责任。亲子之情是与生而来的本性,既不可解也无需解;君臣之义是屡见不鲜的社会秩序,既不可逃也无需逃。对于父母、君主,要使其“不择地而安”、“不择事而安”;对于自己,则要内修以上,以臻“安之若命”之境。因为唯有“安之”,才不会受到哀乐之情的干扰纠缠,而能够“安时而处顺”。
当灾祸无可避免地来临之时,负面情绪不免随之而生,如何能“安之”?“安之若命”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极高的修养境界,或许我们还可以往上推论,能有这样的修养境界者,恐怕曾在生命中遭遇不少逆境,在一次次的反观自省、去累化执之后,才能“安之”。
对此,为人臣者只能去除私意造作,顺应自然情势而行事,哪有时间去贪生怕死、自寻烦恼呢?而且当人臣致力于求生避祸之时,“悦生而恶死”的念头,反而会让他因为过度执着而无法判断当下的形势,更遑论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灾祸反而因此临头。
那么,处世的“实战技巧”为何?“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字字句句都是入世已久的“孔子”的肺腑之言。这些看来琐碎的老生常谈,正是明哲保身的指导原则。只有深谙人世间事务运作的复杂多变、难以预料,才能归纳出诸多处世之理。
庄子画像
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出“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正说明庄子也认同亲子之情是天性表现;而君臣之义是社会伦理。正是这些,构成了人伦规范,而此规范架构了人间秩序,社会因此而井然有序。
然而,个体也因此隐没于群体之中。人作为一个存在于世的个体,几乎不可能置身于人际关系网络之外,所以也几乎无法避免“两难”的困境。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出,这些人世的牵绊、责任,是无所逃避、也不必逃避的。
这呈现出庄子与避世之士有所差异,庄子并非一般“与鸟兽同群”的隐士。庄子想要传达的处世技巧,也说明了庄子确实是经过世事历练的入世之人。然而,“无所逃”一语却也明确表达了庄子曾有想“逃”之心。
就孔子而言,“郁郁乎文哉”的人伦秩序、克己复礼的生命追求,是仁心的实现;然而,对庄子来说,这却也可能是人与自然的破裂之始。
但是,就多数人而言,不可能免除生而为人的责任,人非入世不可,那么如何才能达到逍遥之境?如何才能在群体之中保有个体的自由?在庄子眼中,了解人情世故、理解人性之常,才有可能顺势而为,但这只是外在处事原则而已,要在变动不居的人间世悠游自得,不能只是死记生存法则,而是要灵活运用、见机行事,而这,必须依赖心灵的平静中和。
德荡乎名,先存诸己
《人间世》中还有一则“颜回见仲尼”的记载。故事起源于颜回希望到卫国去,遂向孔子辞行。颜回一开始秉持着儒家一贯的信念,认为唯有感化卫君才能救济卫国百姓。孔子则警告颜回,不可过于轻忽自身的危险性,否则将招来杀身之祸。
“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
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全,又如何能谈救人呢?颜回自身的修养境界还未成熟,就急着“济世救民”,这种不顾己身、一意孤行的行为,只是为了求取美名罢了。
《孔子》——孔子剧照
“德荡乎名,知出乎争。”
人们为了争名、争胜,是以“崇德”、“尚智”,此谓“德荡于外”,因而导致互相倾轧、祸乱不断。颜回只看到卫君的罪恶,却未能意识到自己“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其实也是一种想要凸显自我、贪图美名的罪恶。
谈仁义道德,把自己当成“善”的一方,事实上,也就是把对方视为“恶”的一方;认为对方需要“痛改前非”,在这样的主观心态下,对方能平和地接受“感化”吗?更要警觉的是,对方是操控生杀大权的一国之君,自己如何能不忘初衷、全身而退?
“目将荧之,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
这一段描述,何其生动!多少原本奋不顾身的士人,在实际面对君王时,正是如此畏缩地败下阵来。这更说明了庄子非常了解士人在政治中的困境。
儒家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热忱,其实正是“至己身于不顾”的悲哀。况且,这种热情,背后是否完全没有“私心”存在?儒者口中所标举之“仁义”,是否真的是普世恒存之价值?儒者眼中的是非,又是否真为不可改动之判断?这些都令人存疑。
颜回提出“端而虚、勉而一”的办法,想以端庄谦虚、勤勉专一的态度感化卫君,也遭到驳斥。玲珑认为,颜回的办法仍然是源于“成心”,即由“成心”而发,自是而非彼。谦虚勤勉出于畏惧,仅为表象,并非由真心而出,当然不足以化人。唯有真切地反省生存的困境,才有扭转“成心”、脱离困局的可能。颜回既不能克服自己求名的欲望,也不能感化卫君,最后的结果不是表面妥协,就是因为多言劝诫而被卫君杀掉。
庄子画像
根据《史记》的记载,庄子曾为“漆园吏”,这样的经历想必让庄子对于政治生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庄子并不着眼于帝王之治道,而是努力为平凡人找出解脱之路。
既然不可能完成复归小国寡民的理想,人们就必须思考如何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生存之法?又如何在君臣关系中找到平衡之道?
在《人间世》中,庄子屡屡借着孔子之口,说明处世的艰难。在他心中,孔子入世最深;因为入世最深,所以最能了解君臣关系的紧张对立,亦最能了解要上臻“乘物游心”之境困难重重。所以,借孔子来说明《人间世》,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以上就是关于读庄子《人间世》所体悟的处世智慧全部的内容,包括:读庄子《人间世》所体悟的处世智慧、庄子人间世第三章译文、庄子人间世四句是什么等相关内容解答,如果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