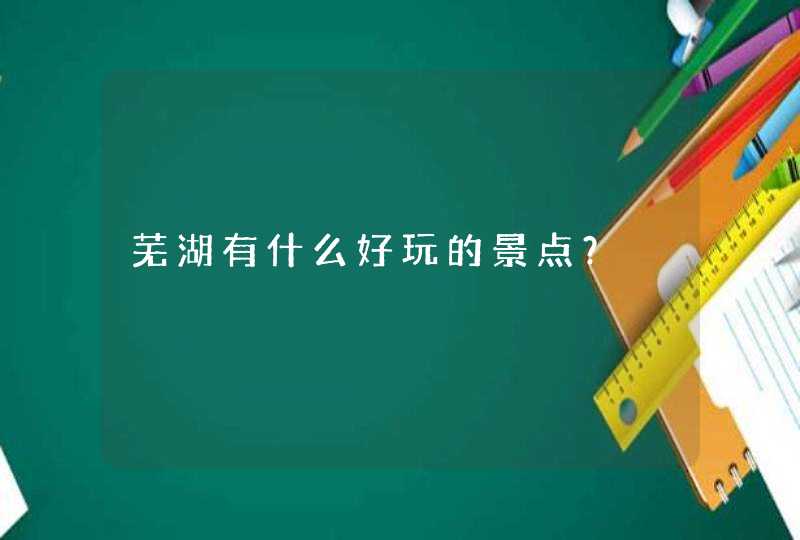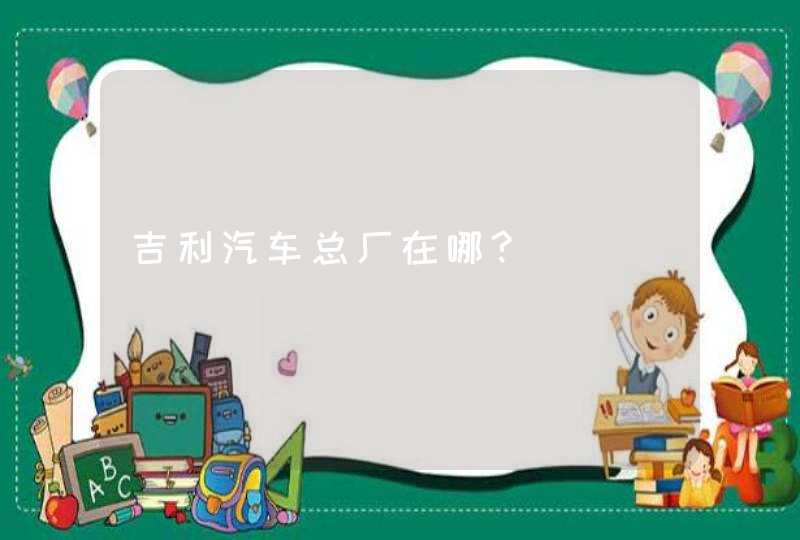“阿里环线”系列游记,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游游走走故事下酒”阅读全部!
转山,特指西藏阿里地区的神山岗仁波齐,是旅行者一生必走的徒步路线。昨天是转山第一天,22公里,我们走到了止热寺。
D8、止热寺—祖楚寺(转山)
次日醒来,冈仁波齐依然静静地伫立在窗前,清冷无声,动人心魄。
转山第2天最艰难:24公里,要穿越海拔5700米的垭口。山上可能有炎阳、暴雨、冰雪,下山的碎石路特别陡,对体力要求极高。
结果是:早10点出发,到达宿地祖楚寺是晚上10点,天已经黑透。12小时,平均时速2公里,对徒步来说太慢了。正常速度是5公里。
依然有专人陪我,我依然落到了最后。什么叫力不从心?就是你明知道给同伴带来了麻烦却无力改变。我一直认为人对团队的愧疚之心是驱使转山完成最重要的力量,当然,转山之路只要你跨入,就没有回头路可走。
出止热寺是一片乱石坡,满目红石,称为“红石滩”。石头上的红色苔藓据说是一种微生物,是有生命的原始藻类,在高原特有的生态环境内得以生长,但生长规律科学界还没有圆满解释。
安静的乱石坡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嘀嘀嘀”,极短促的吹哨声。这是土拨鼠,又称旱獭,肥胖,却灵活。你追过去,它会马上消失在地下,从不远的地方钻出地面嘲笑地看着你。
贫瘠的土地上怎么会养出如此肥硕的土拨鼠?查资料,知道它平均体重4.5公斤,素食,每天可以吃5公斤蔬果。
这一天我们见到无数的土拨鼠,它们洞穴极多,反应灵敏,叫声短暂、清晰、有力。它们经常出现在路边,双脚站立、警觉地看着我们,我们不动它就不动,人稍有反应就落荒而逃。
我们猜测土拨鼠的天敌是流浪狗,在西藏经常可以看见流浪狗配合作战抓土拨鼠,一狗守一洞穴然后突然发起进攻。这小东西太机敏了,人对它毫无办法。恐怕单条狗想抓它们也并不容易。
乱石间,我们还看到两只嬉戏的野兔追逐打闹,动物的世界很祥和。
爬上红石滩的缓坡,回望止热寺,昨晚的宿地已变成眼前的风景,那座极小的营地,白色的房子,就是昨晚的住处,我此行最难受、也是最后高反的地方。
同屋说我昨天晚上呼吸急促,似乎随时要停止呼吸,我当时是完全喘不过气来,半坐才稍觉舒服。
止热寺海拔大约5200米,住处没有水也没有电。旱厕在屋外,居然面对神山,让人背对着不是,正对着也不是,晚上天黑,上厕所基本就地解决。寒冷,好在床铺还算干净,也不潮湿。
出发前,塔钦客栈老板娘提醒带睡袋,“所谓宾馆就是几张床架子,被褥,你们躺不下去,转山的藏人住过的,多年不洗,也无水可洗。”我们猜测止热寺宾馆刚建起不久,所以还算干净。
不能洗澡不能洗脸,没关系,寒冷时可以坚持。没有电真是一件烦恼的事,相机、手机不能充电很要命。去西藏多带几块相机电池,多带几个移动电源尤其是插线板非常必要。到住处往往累个半死,你是没有力气半夜爬起来换充的。转山宿处基本没电,如果相机没电,你会后悔。
缓坡结束开始爬山。据说转山路是信徒们走出来的路,本来是没有路的。前面一部分应该经过了整修。
神山一直伴随,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膜拜它。天空露出了蔚蓝色,天晴了。不过很快,老天就会让我们尝尝暴雪和冰雹的滋味,来考验我们这些转山的人对大自然的敬畏。
我又不行了,几步一歇。能看见同伴的背影,并不远,最多几百米,可就是追不上,我根本没有力气去追。休息的时候还是有事做的,拍照。上上下下,拖远拉近地仰望神山。
我们要路过一处天葬场。
只是一个普通的山坡,乱石成片,正对西南方的神山。但实在并不普通,各类衣物散乱地扔在地上,或者套在石头上,石间有大片人发,触目惊心。为免看客们不适,对天葬我就不过多描述,细节照片也忽略而过。
对藏人来说,面对神山告别世界算此生功德圆满。
转山路要穿过天葬场,是要让转山者感受生与死,感受生命结束时的无奈与肃穆吗?据说转山人都要留一件东西给神山,无论是什么。
同伴们开始登山,我却又坐下了。回看走过的路颇有成就感,望将走的路却心存畏惧,那是卓娅拉山口,海拔5700米,转山途中的最高点。
休息时和藏人侃侃天。老太太76岁了,据说已转过16圈,令我羞愧。
路遇中科院几个调查动植物多样性的北京人,雇了3头旄牛驮着调查用的各类仪器。转山可以雇背夫,背夫兼做向导。不过在我看真的不必要,一路有吃有住干嘛把行李带在身上?而且转山就一条路,想走错路都难。
从照片看,担任领队的女同学已经把登山杖给了我,照顾无微不至。虽然总找理由休息,但山还是要爬的,没有退路,路还得靠自己走。
下雨了,我们加快脚步。不一会,雨变成了雪,再后来,雪变成了雹子,打在脸上生疼。山体很快铺上了厚厚的一层雪,一层冰。天空昏暗一片,暴雪和冰雹飞舞,肆意,砸在脸上。
一个朋友陪着我慢慢走,领队女同学见我们久久不上来回来接我。转山路上这是不小的情谊。不过我没时间歉疚,雪太大,视线极差,快速登山,向顶峰前进。
山顶挂满经幡,光线实在太差没法拍照,或者根本没有力气去拍照。冰雪交加,必须快速离开。没有其他人,停留并不安全。
我的脚步突然轻快了许多,才意识到高反已彻底离我而去,反倒是2位美女同伴跟不上我。
我在前面开路,跑着下山。下山路乱石成片,多是小石子,下山的惯性带着我往前奔跑。这其实很不科学,容易摔倒,对脚指头损害也很大,结果,我右脚有个脚指头死了血,变黑。
跑累了,休息一会,在冰雪中瑟瑟发抖。突然想拍一张自拍照,看看自己究竟是什么狼狈样子,这是本人史上第一张自拍照。照片没有背景,不是没有,是雪太大,一片白。
脸色不好,一路上脸色都非常不好,开始以为是被高原的射线晒黑,后来才知道其实是严重缺氧。在西藏,嘴唇一直枯裂,所有人都是,抹唇膏也没用,但下到平原马上恢复。
下山的路有时候是没有路的,雪盖住了,看不到路。你不知道雪下面是什么,不敢轻易下脚。摔一跤不知道是什么后果,救你的人都没有。
转山的路本来就是踩出来的路,没有路,也就有很多路。要跟紧藏人,他们常年转山,能找到路。
有段路下坡最急,感觉超过60度。坡上满是乱石沙子,根本立不住脚,很危险。但山坡上又满是红石,很漂亮。不过你基本停不下脚步来欣赏。
我们在这段山顶上停留了一段时间。
海拔下降,雨雪小一些,天空也明亮了不少。我们所立之处与对面的山峦间有宽阔的山谷,溪水从远处流过来,在沟底蜿蜓而去,溪边那条路就是我们将要走的路。对面山顶云遮雾绕,山体略隐略现。如果天空再明亮些,这该是多么美丽的风景。
停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几条流浪狗陪着我们一直走到这里。佛教讲究众生平等,狗和人一样也是生命,也被尊重,所以藏人爱狗。流浪狗极多,不缺食物。
下山时,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几条一直陪着我们,陪伴不下10公里。它们不惧怕陌生人,也不跟人亲近,就是陪着你走,默默地跟着你走。你休息它也休息,你走它也跟着走,不离不弃。它们是知道转山之路太辛苦,人需要陪伴吗?
溜下山来,依然乱石成堆,远处有处白房子,是家藏茶馆。有甜茶,也有方便面,就这两样。同行的伙伴们在茶馆等我。喝杯热奶茶,泡包方便面,饿了。10元一碗。
有几个藏人在茶馆休息,于是过去聊天。语言不通,沟通困难,倒是孩子汉语说得不错,勉强对话。不过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傻笑,我也点头傻笑。
他们用奶茶冲糌巴,泡一种类似油饼的面食,手指头自然是要伸进去搅和的。他们热情地让我,我不好拒绝,尝试吃了口饼,似无感觉。
少数民族再汉化,习惯依然是习惯,难以改变的。有个藏族小姑娘吃泡好的方便面,一样是用抓,不用筷子。
合影留念,继续前进,离当晚的宿地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开始一段沿河而行,满是泥泞,后来路稍干燥点,走走停停,不断有掉队的人员,我反而成了收容队,呵呵。
陪伴我们的小溪已经变成河流,右前方是冈仁波齐,我们转到了神山的东边。边走边听“嘀嘀嘀”土拨鼠的叫声,这东西太多了,你不想听不想注意都不成。前路依然漫长,体力消耗极大,可目标点依然遥不可及。
天完全黑下来,已是晚上10点,远远看见灯光,听到狗的合唱,祖楚寺到了。先前已到的朋友传来消息,说宾馆已经找到,晚餐没有问题,正在准备羊肉炖面,还是大碗的,听得大家哈拉子掉了一地,顿时有了力气,奋勇向前。
等我们赶到,却大失所望。
所谓宾馆,其实是一排临时性的活动板房,床铺较新还不错,没水,好在有电。厨房在板房后面,面条才煮上。老板是藏人,只会做两样饭,面条和鸡蛋炒饭。25元一份。
面条端上来,没见到肉,沙子倒是不少。第二天早晨我们决定自己炒饭,炒出来却发现饭是夹生的。我吃了一口就放下碗。
草草吃完,回房睡下。一宿无话。
更多游记与攻略,请关注个人微信公众号“游游走走故事下酒”阅读!
好几次梦到亚丁,梦见的都是自己的肉身,像一截麦秆,倒伏在地上,面目模糊。
我看着它,就像金蝉子取经归来在凌云渡,看见上游飘下来一个死尸,半空中却有人说到: “莫怕莫怕,那个原来是你。”
海拔2000到海拔4800,全程35公里,负重行走整整15个小时。
行走,行走,行走……15小时只做这一件事,在此之后,那个原来的我已经死去,用一场无法止息的行走,换来生命的脱胎换骨。
一路上朽木狰狞,荒原千里。天地宏伟,肉身渺如草芥。
高原瞬息万变的气候,从阳光温暖的摄氏28骤降为零,忽然就雪山冰雹、雷电交加。
缺氧。身体抵达极限,几乎死亡的幻觉。像是做了一场梦,只有太阳穴一锤一锤地钝疼无比真实到麻木。
没有马和背夫。只能咬着牙闭着眼勇往直前,可以休息,却不能放弃,因为你从来就没有退路。
你觉得自己从天堂掉入地狱,又回到人间。
却终于可以看清楚:信念,究竟迸发多强的力量?
那天我们五个人凌晨六点就出发了。天还没有亮。
找了一个向导,带我们走的是藏民转山的路线。
向导大叔是土生土长的藏族人。五十多岁,黑红的脸,汉语有限,总是憨笑着。他穿一件看不清颜色的迷彩军大衣,铺盖卷和干粮打成包袱背着。他对这条路很有经验,告诉我们今天会很苦,预计十多个小时,要走到天黑。
这不是一条寻常路。
从卡斯村出发,穿越一段生长着茂密原始森林的峡谷,当地人叫做“地狱谷”。
再走一段高陡的上坡“天堂路”,远眺央迈勇、仙乃日两座神峰。
最后下山,抵达洛绒牛场,回到“人间”。
当村口的经幡消失在视野中,溪流成了唯一的路标。越走越荒凉。零星的玛尼堆、水边的独木桥,成了人类仅存的遗迹。
我默默数着,大概数到第11到独木桥,我们离开了溪流。
大叔把空可乐瓶浸在泉水里,灌满。山上不会再有水源了。
抓绒衫已经被汗濡湿,而令人腿软的大陡坡才刚刚开始。
森林暗无天日。满脚树根与滑腻的苔藓。被菟丝攀附的树会逐渐死去,自然死亡的树木轰然倒下,变成蘑菇和菌类的襁褓。垂下的菟丝像长发及腰的女巫,面目狰狞。
这里是地狱谷。好像梦枕貘笔下百鬼夜行的外景地,每一个树洞后面,隐藏着一颗窥视的眼球,远处传来怪鸟的哀鸣,光天化日之下,仍使人后背发凉。
最初是每40分钟休息一次,后来,休息间隔越变越短。休息的时候能站绝不坐,因为一坐就站不起来了。
我的先生崔导学体育出生,一马当先。桃子小姑娘瘦瘦的,但她跟男朋友从小爬山长大,两人并列第二。唯有我跟小胖子远远落在后面,做一对难姐难弟。我身高164,体重45kg。
已经顾不得理会崔导的催促了。我走得像个老太太爬楼梯,小碎步,少说话,小口喝水,用瑜伽课的腹式呼吸来调节心率,心跳控制在140以内。实在走不动的时候,就默念心经,放空杂念。
可是仍觉得太艰难了。稀薄的氧气考验着肺活量,更用力的呼吸,似要将肺撑破一般,才能维持基本的活动能力。没有空气,每一个动作都变成慢动作,一旦用力过猛,太阳穴疼的像爆炸一样。
所有争强好胜的心都扔掉,不要做冠军,我只想做那个活着走到终点的人。
森林戛然而止,在一段狭窄的羊肠小路的尽头,眼前突然豁然开朗。
阳光温暖如瀑布,倾洒在头顶,晃得我闭上了眼睛。
感觉好幸福……非常幸福。
难怪人们说:这是一条通往天堂的路。在经历阴森陡峭的地狱谷之后,颤抖的双腿仿佛欢呼着,迎来一段段平缓的坡地。海拔却在不知不觉中变高了。
碧绿的青草地中,成片粉白、洋红的杜鹃,点缀着冷灰松绿的寂寞山谷。万里晴空水洗的蓝,云朵是没有一丝杂质的白,灵魂仿佛也被净化,变得无欲而纯洁了。
远处洁白的雪顶,就是稻城三神山之首、海拔6032米的仙乃日。
相传三位菩萨为度化众生,化身三座雪山。观世音菩萨化身仙乃日、文殊菩萨化身央迈勇、金刚手菩萨化身夏诺多吉山。
六月的高原,雪线已褪却,却并未完全融化。雪线以上没有植被,岩石裸露。岩石含有一种类似于云母的物质,能反射出银色或金色的光线,远远看去就像一座座金山银山,光耀夺目。
她如此庄严神圣,站在雪山脚下,心中很难不涌起爱慕,和一阵顶礼膜拜的冲动。
山里常能看到一些石屋,很小,就地取材用常见的页岩片搭砌。那是藏民自建的休息站。
屋子里有灶,有金属的水壶和器皿,可以生火,门口用油纸挡风,还有两根树棍,大叔说,夜里用来顶住“门板”,以免野兽侵扰。
山上有很多挖虫草的藏民,虫草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一年只挖两个月。每天天少则三五棵,多则十几棵,按每棵60元的收购价,收入能达到4-6万,比修路和旅游接待都挣得多。
虫草是菩萨恩赐的礼物,孩子的学费,女人的嫁妆,皆从中来。
2个月,吃干粮,住在山上,就在那种简陋的石屋里,不能与家人见面。虫草隐藏在草底下,和草甸一个颜色,费眼力。男女老少,趴在地上,用手扒着草皮,鼻尖贴着地面,一寸一寸搜索,哪怕只有一小株叶片,都是希望。
看见我们这些山外来客,他们露出质朴的笑容,操着不流利的汉语说:“要虫草吗,刚挖的虫草,买一根吧!”
坐在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的你,假如不是亲眼所见,永远无法想象高原的贫瘠与艰难。
早就超越了生理需求的你,可能也无法想象,如此用力的拼搏,无关自我实现,仅仅是为了活下来,吃饱饭,能上学。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活下来这三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有天我到了珠峰上海拔第一的天葬台,听喇嘛讲那些遗物的主人:早夭的婴孩,坠下山崖的少年,寿终正寝的老者……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离开人世,却统一被剥除衣服还原成胎儿蜷曲的姿态,经受血与火的荡涤。肉体献祭苍鹰,灵魂归向天际,什么也不留下,这就是高原,生死太常见、太平凡,所以看得淡。
也遇到过转山的人。相逢一笑,说声扎西德勒,他们点点头,口中仍喃喃念诵经文。有些人在禁语的修炼期,不说话,只是磕长头。修行,是有限生命中唯一的灯。
我们找到一间无人的石屋,就在神山脚下,生火吃午饭。
向导把泉水架在火上,煮酥油茶喝,拿出馍馍啃着。我们也取出各自的干粮用力地咀嚼。窗外是万丈深渊,流云漫卷,一道绝美的风景下饭,干粮也不那么难以下咽。
向大叔讨一口茶喝,黑乎乎的砖茶放了酥油,咸,腥,说不清什么滋味,我却喝得如同玉液琼浆一般。
吃完躺下休息,几乎是一瞬间就被瞌睡虫放倒,睡着了。
这一觉睡了一个小时,醒来一看,世界却已经变了颜色。太阳不知道去了那里,央迈勇的宝顶已经完全隐没在乌云中。
向导大叔催促我们快点动身,要变天了。
我懵懵懂懂地看着仿佛要坍塌下来的乌云,还不知道“变天”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马不停蹄的往前走,乌云越来越厚,天低的令人喘不过气来。下雨了。
江南的雨,柔软绵长,淅淅沥沥,就算不带伞也很浪漫。
高原的雨,像鞭子抽,像小刀子割肉,冰冷的,打在脸上生疼。
一路上欢声笑语的小胖子终于笑不动了。他好像感冒了,有点发烧,几乎不愿意再开口说话。五个人以极慢的速度前行,苦不堪言。
可这恶劣的天气并不同情我们。不久,竟下起了冰雹,豆大的雪粒子打在冲锋衣上噼啪有声。浑身颤抖,牙齿咯咯作响。
之前遇到过两位游客,从亚丁来,问我们哪条路通往稻城。一身背包客打扮,没有向导。看这天气,还得穿过地狱谷,真替他们捏一把汗。
雨时落时止,偶尔一缕阳光拉出几条斜线,更多的时候只有冷雨狂风。冲锋衣已经进了水,手指冻得僵直。虽然风景很美,按耐住强烈的摄影渴望,我把相机用塑料袋包起来放进包里,一心一意赶路。
忽然,眼前出现一面碧蓝的湖水,每个人都精神一振。
牛奶海到了。
这意味着,我们离营地还有三分之一的路。
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浮现出热腾腾的酥油茶和温暖的睡袋,还有篝火在晃动。
那片海子,越走越近。厚厚的冰川反射着湖水的蓝光,像一颗镶嵌在银色戒托上的蓝宝石。
嶙峋的岩石和草甸之间,盛开着只有海拔4000米以上才会盛开的格桑花。这种花呈淡紫色,初看不显眼,像一堆干枯的柴火棒子,一旦它花开连片,景象蔚为壮观。奇怪的是,那种紫色,不管用什么相机去纪录,都远远比不上肉眼看到的那么鲜艳生动。
格桑花是高原的象征,这种花带刺,顽强,就像藏族女人敢爱敢恨的个性。 藏族的女人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她们可以是温柔慈祥的母亲,也可以是泼辣倔强的情人。
牛奶海是一片群山环绕的谷地,从坡上下到湖边,看着很近,还有十分钟的脚程。
一大群野生的岩羊湖边吃草。它们始终谨慎地保持着200mm焦距的距离,但这样面对面地看着它们还是第一次。
路边一个很大的玛尼堆,伞状的五色幡旗下,堆满转经人和行者们从各处带来的石头。散落一地纸片,捡起一张,印着经文和一匹长着翅膀的马,这是转山的人在登顶时撒出去的风马纸,传说能够让人快速达成愿望。
我觉得这张纸很漂亮,随手揣在口袋里,很快就忘了。
能不能不走啊。好想就留在湖边露营啊。
但我们还得在天黑前感到营地。离开之前,我最后一次用眼睛扫描了山川全景,把这美丽的地方一寸一寸定格在回忆中。
从牛奶海到终点洛绒牛场,基本上是平缓下坡和石阶。海拔慢慢下降,耳鸣的感觉略缓解了一些。可是雨却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
都说上山费气、下山费腿,我已经感觉不到腿的存在,只是机械地行走着,别让自己倒下。这一段路,回忆起来支离破碎,记不清楚走了那些地方,路过什么风景,只记得衣服冷湿湿贴在背上,又累,又饿,又头疼欲裂,口中念着阿弥陀佛,别感冒,别高原反应,平安回家。
青石板的阶梯泡在雨水里,格外湿滑,一侧是山体,一侧是毫无遮拦的悬崖,最窄的地方仅容两人侧身而过。善良的向导大叔抓着我肩上的背包带子,说:“不怕,带你,不怕。”
他好几次说帮你背包,帮你背包。我说:“大叔,你年纪跟我阿爸一样大,我怎么好意思把行李丢给你?”他笑了,脸上褶子都舒展开来:“哦呀,哦呀!(藏语:好)”
这一段路走得确实太辛苦。大叔其实在山上喝了生的冷泉水,就已经有点不舒服,拉肚子了。但他一直忍着,怕我们担心他,一直把我们送到营地,我才知道,赶忙翻出包里的诺氟沙星给他吃,他却一直在说谢谢。
一路上受他的恩惠照顾,我说一百次谢谢也不够。问他要什么礼物,他听不懂,还是“哦呀,哦呀!”笑着。说了半天,终于明白我的意思,可他不要别的,只要我给他寄一张布拉宫的照片,好供奉在家里,日日遥拜……
天黑之前,最后的艰难跋涉终于接近尾声。山穷水尽之处,树木掩映之中,渐渐出现一片苍翠的草原。
蜿蜒的小河在碧绿的草甸之间穿行,河床上洒满了金灿灿的沙砾和黝黑的卵石。年轻的牧女牵着栗色的马,构成一副静谧而又唯美的画面。
这样的画面,以往只出现在梦中,我一度以为自己太累出现了幻觉。
我的嘴唇已经冻僵,双腿也已经麻木,感官一点点失灵,连疼痛都感觉不到,但我的耳朵还没有消失。
一阵叮当的牧铃声,从远处渐渐靠近,越来越近……
崔导在身后举起了手机,拍下了我摇摇晃晃的背影,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视频画面里,迎面跑来一群马,欢快地从我两边分开,就像礁石分开了湍急的河流。我一人呆呆伫立在草原上,举着手机,既没有躲避,也没有说话,好像沉浸在另一个无声的世界里。
当马儿一齐朝我奔涌而来,我感受到地面在震动。
它们睁大好奇的眼睛,笔直冲向我,然后猛地急转弯,擦身而过。
我忘记了闪躲。也许我根本就知道,它们在用眼神说: 我们之间绝没有伤害发生。
洛绒牛场。我们到了。终于到了。
孤寂的旅程,无论多少人陪伴在身边,与疲倦挣扎的是孤身一人,得登顶感触的亦是孤身一人。眼眶一阵一阵发酸,喉咙发紧。你问我有多感动?这是注定不能共享的,须一步一个脚印亲自得证,没有捷径。
我以为到了洛绒牛场,一切自虐就会马上结束。但是并没有。
从洛绒牛场到游客中心(龙龙坝)的宿营地,还有12公里的路程要走。幸好都是平坦的草原。太阳已经落山,周围的一切被夜幕染上了深深的靛蓝色,一直到晚上九点,我们才走到了游客中心。
游客中心还在装修。这就是景区封闭的原因。
工人们已经下班,聚集在一起烤火,看见浑身湿漉漉的我们,马上让出最好的位置,给我们烘衣服,倒酥油茶给我们喝。
这些工人来自四川、河南等地,负责景区的重修与建设,七嘴八舌和我们聊起来。
我们来的时候,村长说,游客中心可以搭帐篷借宿。一个大姐说:以前也有徒步穿越的游客在此地借宿,搭帐篷,或者拼几条长凳铺上睡袋将就一晚,次日下山。
我们已经把衣服脱下来烘,睡袋铺好,忽然门外走进一位景区领导,说这里没装修,接待不了游客,要立刻下山。
五人大眼瞪小眼,傻了。
下着大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小胖子还发着烧,呼吸困难得跟拉风箱似的,再来回折腾恐怕得弄出肺水肿来。
向导大叔也帮我们跟领导沟通,两人说的藏语,说了什么我听不懂。
领导打了几通电话,最终他告诉我们,可以找一辆观光电瓶车,送我们出景区,找一个家庭旅馆住下,第二天早上回稻城。
虽然千万般不想动,电瓶车跟旅馆也得自费,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有地方住,总比睡长椅要好得多。
坐在四面透风的车里,冷雨无情,刚刚烘干的衣服又一次淋湿。
头顶炸响着霹雳,闪电照亮四周数十米高的松树,格外狰狞。
崔导解开他唯一挡风的衣衫,把我紧紧裹在怀里。我打着冷颤,手伸到口袋里取暖,忽然摸到白天捡到的那张风马纸,毫不犹豫,伸手将它抛向车外无穷无尽的黑暗——
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吧!
再见了!稻城……
梵七七,设计师、旅行摄影师、自媒体写作者,“慢旅”创始人。喜欢慢节奏旅行,深度体验当地生活。三年来行走东南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地,追随玄奘足迹,寻找佛陀圣地,对焦生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