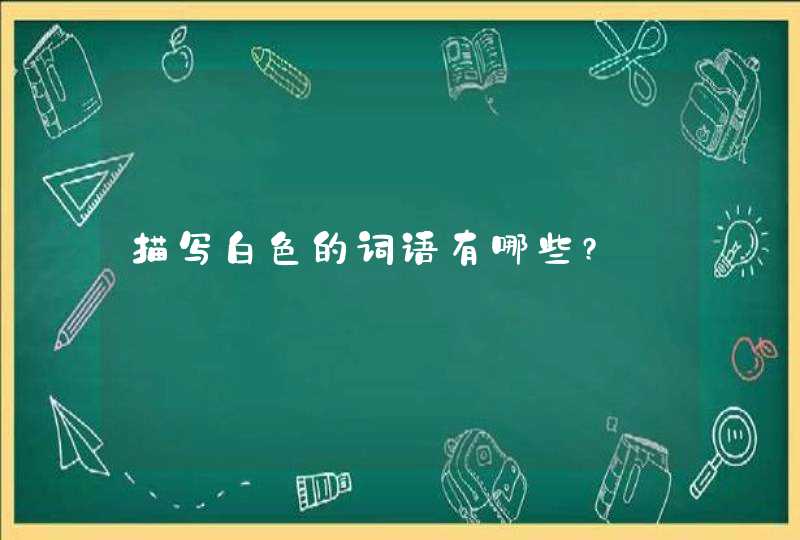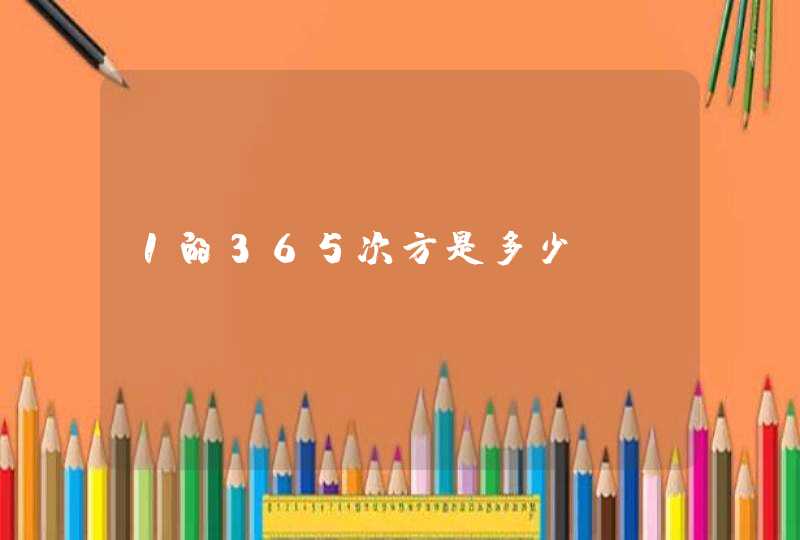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失败,导致安庆失守。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天京已危,天京保卫战进入决战阶段。
这时李秀成再克杭州,席卷了浙西、浙东的大片土地,从战争的局部来说虽然也是一个胜利,但从战争全局来说,并非是对太平军西线损失的一个补偿,更谈不上能起到支援天京保卫战的作用。相反,浙江的军事进展却加深了太平军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浙江的军事胜利,反加速了南京的陷落。
从1862年开始的天京保卫战,主要战役是天京会战和紧接着的进兵淮南。
在天京会战前夕,李秀成为了应对两面作战的军情,主张对天京城下的湘军采取守势,企图先避其锐气,而后击其情归。而对上海则主张采取攻势,计划占领上海;巩固苏杭。这种攻守倒置的战略,反而利于湘军在天京外围实施所谓“似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的部署。
1862年8月,李秀成邀集诸王在苏州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商讨作战部署,决定分兵三路救挽天京。即派杨辅清等军进攻皖南宁国,以牵制敌人的增援部队,派陈坤书等军攻芜湖金柱关,以截断敌军粮道。李秀成则亲率大军迎战天京城外的敌军。
10月中旬李秀成军开始猛攻雨花台的湘军大营,太平军在这次战役中无论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优势,攻势异常猛烈,使远在安庆的曾国藩也承认:
“警报纷来,如在惊涛骇浪之中” “大江南北之危,实如累卵”。
可是历时46天的会战,太平军还是以战而无功而结束。关于此次会战的失败原因,李秀成自己承认:
“八月而来,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在此也。”
其实这只是由于战略错误而派生出来的客观困难而已。李秀成在这次会战中所犯的战略错误,首先是把太平军主力都用在面对面的攻坚战上,作战大量使用火力,可一旦弹药用尽,只得败兴而退。若能将太平军主力插到敌人后方,对敌包抄迂回,截断其供应线与粮道,那战局必然改观。
而且,会战一开始,曾国藩忧心如焚,就是唯恐“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可是曾国藩所虑,却为李秀成所轻。
其次是李秀成在此次会战中未能专心贯注,一获悉“听王败于上海四口,全股就歼,苏昆空虚”就急忙回首照顾自己的领地了,天京会战就因此以失利而告终。
洪秀全为了弥补天京会战的失利,又命令李秀成进行淮南战役,并执行“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这可以说他是对“围魏救赵”计的效法,而失败也更惨重。
所谓“进北攻南”的战略目标有三:
第一、太平军渡江北征,以便使南岸的湘军回救北岸的腹地,从而解天京之危。
第二、淮南是产粮区,占领它可以解除天京的粮荒。
第三、能与皖北一带的扶王陈得才、捻军张洛行等取得联系,重振皖南的局势。
可是这些意图很快被曾国藩觉察,曾国藩亲自从安庆到天京前线,指挥湘军将太平军围护天京城的石垒全部攻破,这样太平军“攻北”不仅未能牵南岸的湘军回救,反而自己非得回救天京不可了。
再说,当李秀成进入淮南地区时,正逢青黄不接,土地无粮,太平军又未得食,饿死者多。李秀成军逢此绝境,那里还搞得到粮食接济天京,至于皖北的捻军张洛行,此时也不幸被清军打败,其他首领所剩无几,皖北的局势一蹶不振。
这样,李秀成进兵淮南的三个战略目标均告落空。
1863年6月,因天京、苏州危急,李秀成被天王诏回天京,太平军在江浦一带渡江。可那时,正逢大江水涨,道路被水冲崩,无处行走。而且,水灾严重,官兵无栖身之所,虽有米却没有柴火煮食,饿死甚多,正逢杨帅、彭帅水军来攻打,此举前后失去战士十数万人。这就是“进北攻南”战略招致的惨重损失。
李秀成在淮南战役失败之后,从1863年6月开始参加苏浙战争。苏州沦陷后,李秀成回到天京。这年11月,曾国藩军已攻陷天京外围的所有城镇据点,根据当时天京所处的不利境地,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外援断绝。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主张,即:
“京城不能保守,曾(曾国藩)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若不依臣所奏,六绝定矣!”。
此主张提供太平天国将领相议时,得到大家的赞同,可是洪秀全拒绝了当时唯一可行的“让城别走”方案。
1864年2月底-4月,湘军占领太平门、神策门外,完成对天京的合围。此时城内的太平军已是无本之末、无源之水,经过4个月惨烈守城战与巷战之后,太平军大部战死,一部自焚。
至此,历时3年的天京保卫战全面失败,天京沦陷它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
02 洪秀全之死因为史料缺乏以及各种史料之间又相互矛盾,导致对洪秀全之死的说法不一。
一说洪秀全“服毒自尽”,如范文澜先生所写的《中国通史》说:“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洪秀全服毒殉国。”
一说洪秀全病逝,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说他1864年5月中旬生病之后,6月1日离世。
综合来看,洪秀全是死前患病,健康状况极度恶化,但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应该是病中服毒自杀,以身殉国。
1864年5月30日,也就是洪秀全死前一天发布了一道诏令:
“ 大众安心,联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
这道诏令表明了天京危在旦夕,洪秀全不愿作阶下囚,决心以身殉国的一个临终嘱咐,他就是在这道诏令之后的次日突然暴亡的。
根据洪秀全当时的病状,并没有患致死的急症,洪仁玕、李秀成等人说他“卧病二旬”、“不食药方,任病任好”,就是明证。所以,把洪秀全的暴亡当成急症致死,恐怕是缺乏根据的。
再从洪秀全卧病以前,已经产生了厌倦尘世之感,期望有龙车载着他升天,与洪秀全后来临死前一天发布的上天堂诏令是前后呼应的,说明了洪秀全早已有应急的思想准备,时候到了,他即以身殉国。
此外,还可以联系到天京危急时,洪秀全曾写诗明志说:
“神爷试草桥水深,为何吃粥就变心?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漓淋。不见先锋与前导,立功天国人所钦!”
当着国破身亡之际,洪秀全既不能接受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进取策略,就只有以自杀的消极行动来表明自己以身殉国的决心。
他的暴亡,与其说是危急症致死,不如说是病中自杀更符合洪秀全的思想发展和当时的身体健康情况。
1862年5月。曾国荃率湘军围困天京。从上海撤回的李秀成部为主力的太平军与湘军在天京城外血战46天,未能解围,李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被拒绝。李率1万多太平军留守天京,同5万多敌人殊死斗争。
1864年2月28月,天京钟山要塞天保城失守,3月2日,敌突破太平门和神策门。
6月1日,洪秀全病逝。
7月3日,地保城失守。天京守军仅剩三四千人。敌军在天京城墙下埋放火药3万斤。
7月19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午,敌军点燃炸药,轰开20余丈城墙,蜂拥入城,各城门都被敌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陷落!敌军入京,“见人即杀,见屋即烧”,把天京洗劫一空,付之一炬,大火七日不熄。
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是必然的。从军事角度来讲,南京是绝地。打开地图看,南京东西北三面处于长江之滨,南方一片大平原无凭无险可据。不说南京北面江面很窄容易渡过,如果敌方据北牵制,主力从长江上游过江,然后从南方突击,南京就丧失全部战略纵深,成为就地背水一战的格局。那么援军来自哪里? 斯大林格勒以付出巨大的牺牲从水上不断输送军队进入斯大林格勒,这才守住了。太平天国所面对的长江北岸却早已被清军江北大营占据了。所以,当清军突破安庆、芜湖随后朔江而上,天京就成了囊中之物,陷落只是早晚的问题了。
太平天国的军事上始终只重视沿江驻扎(比如安庆和芜湖),却没有在长江北岸进行布局。而清军一开始就建立江北大营而后则牢牢扎住江北江南两个大营从而死死掐住了天京的死穴,让天京的军事作茧自缚动弹不得。
天京的天王们不是庸才。他们怎么会没注意到这些呢? 急于做皇帝的虚荣、享乐的短视、内斗的消耗。他们在自身总体实力还远较大清差的情况下就急于建都,建都就要分兵设防,如此布局就会被优势的敌方兵力盯死,处于被掣肘的状况中,无法以自己劣势的兵力主动出击打到大清的地盘上去, 由此保障“根据地”的安全。历史也正是这样演绎,清军始终把握住打沿江重镇,甚至直接攻打天京,迫使太平军主力不得不把主力放在反复与清军争夺沿江重镇和防守首都。明知这是清军“围魏救赵”的明谋阳计,却也无可奈何,如此败局已定。尽管太平天国的将领们也想到了北上用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也实际派兵北上了,但兵力有限,更没有后方接济,总体军事战略的配合,最终北上部队弹尽粮绝而全军覆没。
北伐的失败更重要的是因为内乱。天王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杀得尸山血海,死的死走的走,有限的力量也分崩析离,谁还有心有力组织北伐部队的保障,更还有谁能够有能力去从军事上对北伐部队展开战略策应呢! 最后连驻扎苏州地区的部队都北调守卫天京,这唯一可以支持天京抵抗外敌的通道“虚幻若谷”,以致清军长驱直入!
天京最后陷落难道还是偶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