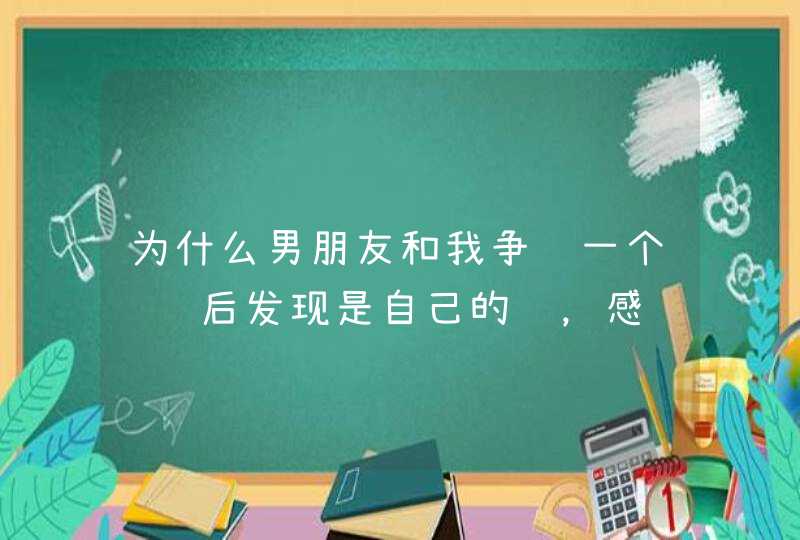阿来在创作中一直保持着小说诗意的叙事风格,让人读后回味无穷。这种诗情画意,一方面是川端康成的情感浸润,另一方面是怀旧而现实,梦幻般的,魔幻而超脱,极其现实而又深刻批判现实的精神。
《尘埃落定》的诗性叙事特征是一种颠覆阅读理性的诗性叙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多重叙事视角重叠;
2.非人格、非典型叙事;
3.叙事逻辑的颠覆;
4.抒情叙事的无主题变奏。
01多重叙事视角的重叠阿来小说诗性叙事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的混合,造成叙事视角的多重重叠。他打破了中西叙事视角理论的诸多规范,是一次全新的叙事冒险和颠覆性叙事。
传统叙事理论根据不同的人称将叙事视角分为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而现代西方叙事学将叙事视角分为三类:零焦点、内部焦点和外部焦点。无论是分为两部分还是三部分,都对不同类型的叙事方法、技巧的局限性、各自的优缺点等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归纳。,既指导写作又指导批评。
但是,第一人称视角不能作为第三人称视角。因为第三人称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是“上帝之眼”,所以作者讲述别人的故事,窥视他们的心理,极其自由地叙述一切内外事件。
而第一人称叙事则要求严格按照“目击者”或“旁观者”的个人经历和感知来讲述故事。只能基于“我”和“我们”的身份和经验,只能有限地讲述自身和他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以符合心理和逻辑逻辑,增强作品的艺术真实性。但细读了阿来的一些小说,尤其是《尘埃落定》,这些叙事视角理论似乎有些捉襟见肘。阿来让这些叙事学的经典理论面对他的叙事文本,成为失语症。
舞剧《尘埃落定》剧照,下同。
在《尘埃落定》中,作者以一个“傻不傻”的二少爷为叙事承办人,由“我”(二少爷)讲述了一个“我”的人生成长经历,讲述了一个在酋长辖区的人生图景。
“我”作为一种叙事视角,本应按照“我”的视角进行严格定义,实事求是地讲述“我”和他人的故事。然而,文本将“我”变成了多重叙事视角的承载者:
第一,“我”是一个真正的有生理缺陷的傻瓜。所以文中很多地方写“我”以愚人的方式去感知、思考、行动,呈现出一系列傻乎乎的样子。
其次,“我”是一个不傻的正常人,甚至是一个聪明人。所以文中很多内容说的是“我”以一个正常人或智者的方式感知、思考、行动,表现出一系列睿智的行动。
第三,因为“我”傻不傻,很多内容只是作者简单地以“我”的身份讲述,所以“我”就成了一个全知的叙述者,这是第三人称视角介入他人心理活动的结果。
整篇长文围绕这三个视角,放在“我”上,呈现出一种杂语交替发声的复调状态。让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同时充当主角和叙述者,显然是一种叙事冒险。中外文学史上真的没有先例。
一些评论家引用福克纳的作品《喧哗与骚动》为例,说明福克纳试图让一个白痴讲一个长故事,但失败了。用西方叙事手法理论来衡量阿来,得出阿来的非理性叙事是致命的疏忽、失败和谬误,可能有削足适履之嫌。
阿来多视角的混合叙述,其实是一种“虚构”,因为二傻少年自己只能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这些虚构的人物是无法用生活或者理性逻辑来解读的。诗歌和诗歌一样,在心灵的倒影下,可以让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诗歌的魅力来源于其新颖、独特、优美、丰富的感受和体验,而这种感受和体验并不是理性的。即使是哲学上的,也是用丰富而丰盈的感性意象来照亮理性的结果。
我们只能把阿来多重叙事视角的重叠当作抒情叙事。这些不符合视角和感受标准的丰富感受,融进了读者对人性、人生、命运的深刻而美好的体验。
因此,试图以某种理性介入作品的阅读,恢复叙事视角的理性设定,确定人名背后的一系列理性规范,都将是徒劳的。
02非个性化与非典型叙事《尘埃落定》诗意叙事的另一个特点是非个性化与非典型叙事。作者以“我”为叙事视角,但不受“我”的身份、年龄、职业、学历等人格特征的限制。他以“我”与作者同构的抒情视角,淡化自己的个性和典型创造,自由想象有意叙事。
按照传统的叙事理论,从“我”的角度来看,一般有两种叙事方法:
一种“我”就是英雄。这样就要刻画出主角的性格特征。“我”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我”的身份、地位、性别、年龄、职业、学历等特征,从而形成个性和典型性。尤其是“我”的语言要有个性,不同人之间的对话也要符合他人的个性。总之,任何事物都应该有个性。
另一类“我”只作为目击者、旁观者等线索人物出现,受本人身份、年龄、职业、学历等性格特征限制,讲述他人故事。通过“我”的个性化视野的过滤,其他人的故事也显得很有特点或者很典型。
随着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兴起,“我”可以描述大量的心理活动,意识与潜意识、现实与梦境、当下与回忆可以极其自由地流出。但作为“我”的意识流,无论是现实还是神话,也应该有一定的特征性人物。
阿来的小说叙事确实有一些意识流叙事的特征,但显然不是意识流,因为他的叙事目的是通过对生活事件的回忆性叙事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经历,有些诗意和抒情,与意识流的叙事目的明显不同。
阿来的小说像是一种“记忆流”叙事,但他将记忆叙事与现实叙事交织得如此恰到好处,让人分不清真实与虚幻。于是,这些经典叙事理论又一次被阿来的小说叙事所颠覆。
在小说中,作者用现在时来表达对所有过去事件的现实再现,包括大量回忆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从而产生无逻辑、非个人化甚至无回忆的叙事效果。读者看不到“我”的个性或典型性,更看不到语言、性格、心理等的成长过程。,随着年龄和职位的变化而变化。
像小说中的“我”,既不个性化,也不典型,也看不到成长过程。因此,有评论者将其评价为叙述上的明显错误和人物性格逻辑上的某种混乱。
但如果从诗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正面解释的。抒情诗不需要写抒情主人公或人物的个性,也不需要典型化。它结合意象,融于特定的意境和境界,含蓄地表达了抒情主体的一种情感、一点感悟、一缕思绪和一些感受。
阿来小说的非个性化、非典型叙事,正是遵循了抒情诗的原则,将无数个“我”的记忆串联在一起。它展现给读者的不是人物、性格、典型性,而是“我”对一系列往事(人生大事、历史变迁、国家命运、人性、理想追求等)的丰富而充分的体验和感受。).
由此可见,服从人物塑造的传统小说叙事学的一系列规范,已经被阿来小说的诗性叙事所打破,走向了灵魂的展示。
叙事逻辑对非逻辑叙事的颠覆,是阿来小说叙事具有诗性特征的另一个原因。
一般来说,叙事性文学作品,无论是现实的、浪漫的、象征的还是魔幻的,都要遵循逻辑规律。或是生活事务的逻辑,或是心理性格的逻辑,或是情感想象的逻辑,或是变形虚构的逻辑等等。,要么遵循客观生活真实原则,要么遵循想象虚构原则。
总之,要有艺术性或者可信。然而,阿来没有这样做。他一方面竭力创造现实主义和可信性,另一方面又竭力颠覆现实主义和可信性。以逻辑与非逻辑的混合叙事策略,将叙事文本变成诗性文本,以诗性的超逻辑张力结构,使不能同时发生或成为事实的事情成为可能,成为真实。
《尘埃落定》的整个叙事充满了逻辑矛盾。作者让一个既傻又不傻的人来担当叙述者,是造成读者和评论者理性解读时逻辑混乱的主要因素。
“我”既是愚人,也是智者。在文本的叙述中,一方面试图证明“我”真的是个傻子,一方面又试图证明“我”很聪明,形成了一个超逻辑的“我”。
再比如,一方面,小说以“我”的自述为蓝本,但在小说的结尾,写着“我”躺在床上被复仇者杀死,我看到自己的血流了出来:
“地板上的血滴好大。我在床上冷了,血在地板上慢慢变色。”
读完小说,读者不禁要问:既然“我”已经死了,那么“我”讲述的这部小说是谁叙述的呢?这是对阅读理性逻辑的又一次颠覆,是超逻辑的。在小说不合逻辑的叙述中,到处都是矛盾:
“我”既推崇宗教,又不信仰宗教;“我”既不追求世俗的欲望,也不排斥这些人类的欲望;“我”既不为自己酋长的高贵身份而骄傲,也不因为自己是个傻子而悲伤;“我”是友好的,也是残忍的;“我”是所有事件的介入者,是旁观者或局外人;“我”热爱生命,体验生命的美好,却不贪生,自然而死。简而言之,一个充满逻辑矛盾的“我”,一个读者无法理性认定的“我”。
因此,整个叙事处于证实与证伪的矛盾同构关系中,挑战读者的理性,造成阅读中的逻辑颠覆。然而,这种非理性叙事诗意地将整个叙事引向了“我”的主观叙事。因此,小说的叙事在客观与主观、现实与超现实、现实主义与虚构之间建立了一种超逻辑的联系,产生了一种超逻辑的抒情诗歌的张力结构。
从而再次将读者引向抒情阅读,让读者从对客观事实的认知中体悟到主观的精神事件,进入抒情主体的情感世界,读出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一种暗示、一种感受、一种向往。
《尘埃落定》诗性叙事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抒情叙事风格,这导致叙事文本的意蕴展示方式向抒情文本的转化,形成小说主题的去中心化,导致多重意义并存,再次颠覆了读者对叙事小说主题熟悉理解的阅读理性。
一般来说,无论叙事小说文本是故事型、人物型还是心理型,其主题都有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者在故事型叙事中,主要情节表现主要矛盾冲突,从而揭示主题;或者在人物叙事中,以典型人物及其典型性格表现主题,从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中揭示主题;或在心理叙事和意识流叙事中,营造典型的情感、氛围、情结、意识等典型心理形成主题;或者在诗歌和散文叙事中,营造特定的意象和意境,象征性地暗示某种寓意。
因此,叙事文本都有相对确定的主题或各种主题。然而,这些经典叙事文本的主题呈现方式被阿来的小说所突破,产生了无主题的多重意蕴共生。
读完《尘埃落定》,我们很难确定这部小说的主题意蕴。小说围绕着“我”的一次经历,讲述了“我”看到的、做的、想到的、感受到的很多事情。读者无法根据自己阅读叙事文本的经验来把握小说的主题。
许多关于小说的评论文章几乎都回避了小说的主题或寓意,因为作者没有设定主题或创作意图。作者所叙述的人物和故事并不服从一个统一的主题设计,文中的事件和人物都是以各自独立的形象存在的。这些相对独立的表意文字和事件有一系列的演变,并不受制于某一种蕴涵设定。
所以整篇整篇文章的内容就像一盘五颜六色的珍珠,每一颗都放射出不同的颜色。我们只能到处看到美丽的闪光,却分不清哪种颜色最耀眼。这种混色的方式,就是小说中揭示寓意的方式。
这样一来,阿来的小说就真的成了“没有主题的变奏曲”。它是一种分散的、无主题的抒情诗。诗人通过对栩栩如生的人物、事件的想象,将“我”对自然之美、世界人生的一系列感受、体验乃至看法融入到这些人物、事件、场景的意象中,表现出不同的体验见解,一路向读者讲述不同的人生体验。
试图用经典叙事学理论寻找阿来小说的理性阅读模式,又一次被阿来小说独特的叙事所颠覆。
总之,《尘埃落定》的诗性叙事倾向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它挑战了我们历史悠久的传统叙事文学的阅读理性,颠覆了传统的叙事理论,建立了独特的个人叙事风格。
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