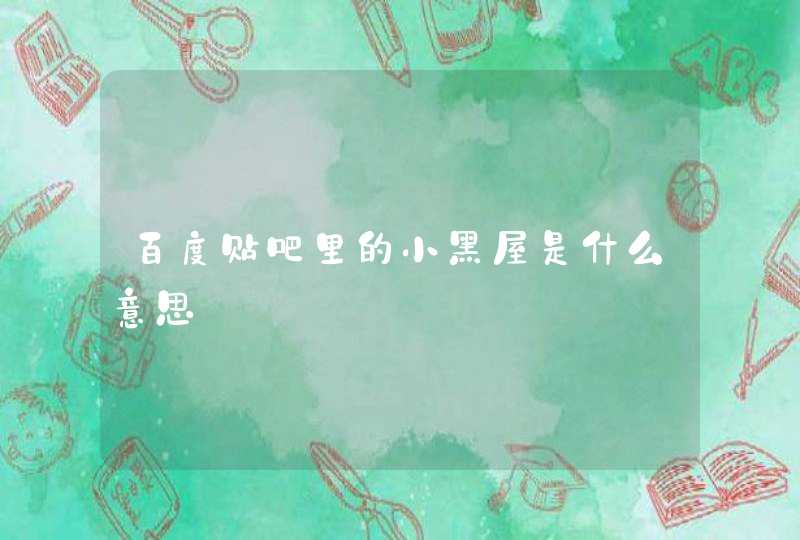读经典
简单翻译下:难以避免的兵力削弱、政局混乱,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混乱国家的做法。
简单翻译下:如今国境内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家里藏着商鞅和管仲的法典,而国家却越来越穷,就是因为空谈耕作的人太多,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
简单翻译下:国境内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家里藏着孙子和吴起的兵书,而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就是因为空谈打仗的人太多,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
简单翻译下:所以明君只要用民众的力量,而不听他们高谈阔论;奖赏民众的功劳,而禁止他们无用的言行。这样以来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了。
谈心得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就已经多次强调这个掷地有声的兴国良策,所以说一堆不如做一句;事要多做,话要少说,做的越多,懂得就越多,这个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韩非在本节就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难以避免兵弱国乱的根本原因:“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就是说现在民众浮夸称赞的,君主以礼相待的,实际上都是祸乱国家的做法和手段。
一方面民众是社会的主题和基本组成,他们是国家发展的底层力量,也是国家好坏直接的体验者,而如今他们所称赞的都是些虚妄的言论,都开始不务正业、耍嘴皮子功夫,导致全国上下浮夸成风!
另一方面当下的君主都喜欢听讨好赞誉的话,对妄言奉承的人礼遇有加,自然就造成臣下一味的溜须拍马,因为讨好奉承就能获得赏赐,这可比苦力农耕、打仗建功容易的多!
国境内的民众也都在讲治国强国之法,家里还都藏着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可国家还是贫困,为什么呢?“言耕者众,执耒者寡”,谈论耕种的人多,拿起农具干活的人少,典型的只说不做。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君主关注的只是清谈,只要家里藏着强国之法,到外面夸夸其谈,君主就会赞许夸奖,却都忽视了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就是人,都没有人愿意干农活了,哪来的物资和财富,国家焉能不贫?
对于强兵之策也是一样,民众也是家藏孙、吴之书,说起来都是振振有词,可真正披甲上阵的人是少之又少,都知道打仗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如今只要能把打仗之事说的天花乱坠,就能收获君主礼遇,谁还愿意去拿生命冒险呢?
所以,韩非子告诉君主”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要只用其力,看行动不听其言;论功行赏,禁止无用言行。凡事都要去做,用实践来验证,用结果来证明做事的成效,成为赏罚的唯一标准。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民众都愿意拥戴为民众谋福利的君主,都愿意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加把力。面对以民众为中心的君王,自然拼命拥护,尽心尽力的做事了。
“蠧”字读dù。
蠧dù的含义:
同“蠹”。
1蠹虫:木蠹,书蠹。
2蛀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部首:虫
部外笔画:16
总笔画:22
五笔86&98:FPDJ
仓颉:GBMRI
四角号码:40136
UniCode:CJK 统一汉字 U+8827
附:
《韩非子》-五蠹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面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参考资料
搜狗百科:>
五蠹原文阅读
出处或作者:《韩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动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面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五蠹对照翻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动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韩非子《五蠹》原文及翻译如下:
作者:韩非。
创作年代:先秦。
1、原文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2、译文
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兵器短的被敌人刺到,铠甲不坚固的伤到自己的身体,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
《五蠹》作者简介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河南新郑)人,身于贵族世家。他和秦始皇的宰相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是秦王朝统一全国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曾建议韩王采用法家主张,实行变法以图自强,但未被采纳。后来韩非的著作如《孤愤》、《五蠹》等传到秦国,秦始皇读后十分欣赏韩非的才识。
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这时期经历了春秋以来约300年的战争动乱局面,结束了奴隶制的统治,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巩固,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也初步确立。要求出现一个统一的安定发展的政治局势,成为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
以上内容参考360百科-五蠹
韩非子《五蠹》解读
韩非子《五蠹》中说:“古时候,人们不用努力做事就足以供养生活,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之间没有争夺。现在的情况与当时不同,人民多而财物缺少,费尽劳力做事还不够供给吃用,所以会发生争夺。尧统治天下的时候,生活极为简朴,现在就是一个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带领人们干活,现在虽是一个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苦了。古人轻易地辞掉天子不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天子的权势单薄;今天的人重视争夺官位,依托权门并不是因为他们品德卑下,而是因为当官的权势很重。所以,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来采取措施,因此刑罚轻不能算仁慈,刑法重不能算残暴,不过结合当时人情风俗行事。所以政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措施也要适合已经变化了的政事。”
这一段话,表现了韩非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与时俱进”。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生活、心理、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也在发生着改变。古时候文王施行仁政使得古戎屈服,徐偃王实行仁义的统治却被楚国灭亡;舜派人手拿盾牌和大斧对着苗人跳舞使得苗人降服,对共工氏跳舞却会惨遭失败。由此可见,不同情况下实施同样的政策,结果却大相径庭。先人的做法在当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是未必适用于当今的社会。统治者应该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制定不同的政治政策,来使天下得到治理。
韩非子说:“孔子算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品行,宣传正道,可是天下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并且真正信仰而服侍他的人不过七十个。真正看重仁义的人还是少数,真正实行义的人还是很难得。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严格执行刑罚。施行刑罚越重越好,而且不随意变更,使人们有所畏惧;国家的法令越统一越固定越好,使人们都知道。所以君主实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也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以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谴责,这样一来,不管品德好还是品德坏的人,都会尽力量为国家办事了。”
这段话,表现了韩非子对儒家思想的排斥。他认为用所谓的仁义思想来教育人民,只能感化一小部分人,并不能达到使全民归顺的政治目的。而作为统治者,单纯的仁慈与理解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将法律放在首位,依照法律治理人民,实行强权政治。只要有功的人就进行奖赏,只要有过的人就进行惩罚。人们本来就畏惧权势,再加上以法律为重的治国方针,便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
韩非子严厉批判了纵横家,他认为这些游说之士只为自己谋求高官厚禄,而危害国家利益,是“五蠹”之一。为了使国家不成为战乱的牺牲品,应把重点放在整顿国内的政治上面,即用法律治理国家,增加财富的积累,坚守城池。而不是听取纵横家口中那些势必亡国的连横合纵的计划。我非常赞同韩非子的观点,连横与合纵只是权宜之计,实行不好还会加速灭亡。修明内政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有效策略。
韩非子在《五蠹》一篇中提到了品行与法律存在的矛盾。“一个人,因为有功劳授予他爵位,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做官才疏远他,却又推崇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它违反了法律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该斥责的和刑罚的,执行起来如此互相矛盾,所以国家的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在这一段话里韩非再次强调了“仁义品行之说”对于治理国家造成的阻碍,而最后提出来的“五蠹”之中的两种:儒学家和游侠实际都是这种矛盾的产物。他们依仗君主对于其品行的赞赏而胡作非为,扰乱政治。其实我觉得不能将罪名加在这两类人身上,问题的根源在于君主。如果君主依法治国,摒弃名声与品行的影响,完全按照刑罚来对人进行评判,那么这两种人自然会从社会上销声匿迹了。
韩非子还提及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的矛盾。“人民所认为的正确的计谋,总是追求安全的利益而避开危险和穷困。前进就要被敌人杀死,退却又要受军法判罪,真是太危险了,人们怎么逃避呢?他们争着去为私家服务而求免除兵役,免除兵役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能安全。”“五蠹”中的“逃避兵役的人”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逃避兵役是人们出于自己利益考虑的正常心理,但却对国家不利。因此作为统治者,要制定法律来奖励耕战的人,惩罚这些逃避兵役不依法行事的人。
“五蠹”中提到的最后一种人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通过金钱买来官爵,使自己的地位提高。韩非子认为他们助长了社会上行贿托情的风气,地位甚至高于从事耕战的人,使得社会上正直的人减少,对于治理国家很不利。同样,君主也要制定惩罚措施,压低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形成国家良好的风气。
总而言之,从韩非的角度看来,治理国家首先要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严格的奖励与惩罚措施,之后拒绝纵横家的荒谬言论,以修明内政为主要努力方向;再次应该摒弃品行与名声,完全依照法律评判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并给予他相应的社会地位;最后要严厉的责罚那些投机取巧、扰乱社会风气的人,形成国家的良好风气。
“五蠹”的原文是: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面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2五蠹全文翻译: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兵器短的被敌人刺到,铠甲不坚固的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现在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说得没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鲁国,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从这方面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变,凭借徐国、鲁国自己的实力,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末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以上就是关于《韩非子•五蠹》之五十二,实干兴邦的富国强兵之道!全部的内容,包括:《韩非子•五蠹》之五十二,实干兴邦的富国强兵之道!、“蠧”字怎么读、《五蠹》原文及对照翻译等相关内容解答,如果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