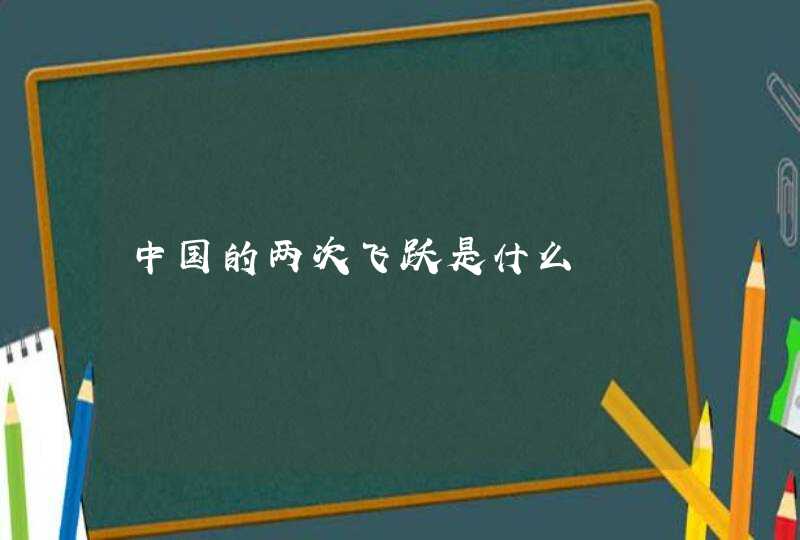这句话语出《论语·卫灵公》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意思是:人能够使道发扬光大,不是道使人的才能扩大
人必须首先修养自身、扩充自己、提高自己,才可以把道发扬光大,反过来,以道弘人,用来装点门面,哗众取宠,那就不是真正的君子之所为。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可以颠倒的。
举例:朱熹注:“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论语集注》)董仲舒天人对策中也引此句,言治乱废兴在于己。今人杨伯峻认为与愿意不合。
扩展资料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是廓大之意,那么道究竟指什么道?儒家、道家甚至法家都有谈及道,但他们的道各不相同。孔子所言之道,是儒家的道,是仁道。因此,这八个字, 字面意思是说:人能够把道廓大,不是用道来廓大人。
但孔子的真意是否就是如此呢?
朱熹曾经解释说,“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将这八个字归结为人有觉与道无为的差别。据《朱子语类》记载:有学生问朱熹怎样理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熹便用扇子作喻,说:“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摇扇,扇如何摇手?”朱熹的解释有些牵强,但毕竟点出了一点,即 人的主观能动性。
钱穆认为,“ 道由人兴,亦由人行。”也就是说,道的兴起与发展都离不开人。这便是人能弘道。而自有人类始,智德日成,文物日备,学思益积益进,渐渐地就有了大才小才的区别。“若道能弘人,则人人尽成君子,世世尽是治平,学不必讲,德不必修,坐待道弘矣。”(《论语新解》)所以说非道弘人。这与《中庸》说的“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一个道理。因此,必然要重视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论语卫灵公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儒家对“人”与“道”关系的基本看法
详解:这句话和前面的有点不同,字面意思很简单。“弘”,“使~光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使道光大,而不是道能使人光大。”然而,字面简单的,往往理解起来更复杂。这个简单的句子,却厘定着《论语》、儒家对“人”与“道”关系的基本看法。
有一个很坏的传统,总把“道”往虚无缥缈中寻去。这种把戏,千百年来一直愚弄着偷心不死之人。而对于《论语》、对于儒家,这种把戏是无效的。儒家从来都是现世的,无论这“道”是何道,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承担”上。在《论语》里,“道”只指“圣人之道”,只和现世有关,只和现世的“人不愠”有关。任何往虚无缥缈处瞎推的把戏,都只能是把戏。
还有一种更坏的传统,就是以“道”压“人”,把“道”描绘成一个虚无缥缈的远景,然后让现实的“人”为这个虚无缥缈的远景垫背。这,比起“一将功成万骨枯”还要残忍。后者,至少还有一个“一将功成”让大家唾骂。而当把“道”有意无意地装扮成虚无缥缈的远景时,则连对它的唾骂都变成此等造假戏剧中的荒谬情节。这种荒谬的悲剧,在历史上不断重复。
但比起下面这种,以上两种就不算什么了。历史上永远不缺这种人,他们以“得道者”、“行道者”自居,以“道”的代表自居,他们成了人间的上帝,他们制定人间的法律,一切违背他们的就成了大逆不道。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却往往是个个道貌岸然,一副拯民于水火的姿态,私下却干尽见不得“人”的事。这种“挟私道以令诸人”的人,难道还少见吗?
而这里的“道”,是大道,是公道,不是哪个人、哪群人的小道、私道。只有“人”,才能使“道”得以光大,离开了“人”,并没有一个“道”可以让“人”得以光大。“道”的彰显,是“人”现世存在的当下涌现,离开当下、现世,只能是虚无缥缈的远景,与《论语》、儒家的“圣人之道”毫无瓜葛。
这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前面曾提到的《论语》、儒家和西学中的柏拉图、基督教、科学主义等的根本分歧。对于后者来说,是“道能弘人”,在柏拉图那里“道”是理智的光芒,在基督教那里“道”是上帝,在科学主义那里“道”是科学;但对于《论语》、儒家来说,是“人能弘道”,理智的光辉、上帝、科学都离不开“人”,没有“人”,这些所谓的“道”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正由于《论语》、儒家的这种精神,才使得西式的宗教在中国从来都没能得到光大。
有着一种西学的思维语境有人可能要问,这样是否意味着《论语》、儒家否认客观的规律?对于《论语》、儒家来说,客观规律的有无并不是一个首要的前提,无论有无,都是“人”必须承担的。在“天地人”模式中,客观规律属于“天地”范畴,构成“人”展现的舞台。打个比方,对于“人”这个演员来说,无论舞台如何,演好戏是最重要的,而好的演员,无论怎样的舞台,都会充分利用构成这个舞台的当下、现实的条件。《论语》、儒家并不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但这只构成“人”活动的舞台,而不构成“人”的表演、显现本身。对于《论语》、儒家来说,“道”只特指现世、当下的“圣人之道”,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本体、本原、规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对于已经受西学影响太大的国人来说,是需要反复强调认识的。
有人把儒家归于西学“人本”主义的范式,完全是无的放失。儒家的“人”,是站在“天地人”的宇宙结构下说的,并不需要一个“人本”主义来“本”人。“人本”一旦被主义,就会失去一切主意,变成意识形态的闹剧。而用西学的“结构”范式来考察儒家的“天地人”结构中的“人”,同样是无的放失。“人”在“天地人”结构中并不是某种构成因素,而是展现,“天地”只是“人”展现的舞台,而这一切都是当下、现世的。这里的“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正“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一种暂时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不知”的人。这两种人构成了所有的人,用现代术语就是包括了构成社会的所有人。
因此,根据“人”的两种不同含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必须至少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对于正“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来说,他们的“闻、见、学、行”能使得“圣人之道”得到彰显、涌现,但并不是他们“闻、见、学、行”“圣人之道”就使得自己得以高人一等、凌驾于别人之上,成为所谓的精英,甚至打着“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旗号行其私道;
其二,对于暂时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不知”的人,“圣人之道”的彰显、涌现并不能离开他们,把“人不知”的世界改造成“人不愠”的世界,不能离开“人不知”的人,并不能打着一个抽象的、虚无飘渺的“圣人之道”去利用“人不知”的人,把他们当成就一个抽象的、虚无飘渺的“圣人之道”的垫背。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归根结底只有一点,就是“道”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只有现实中的“人”才是目的,一切以打着虚无飘渺的所谓“道”为目的,以现实的“人”为手段的所谓“闻、见、学、行”“圣人之道”,都是《论语》背道而驰的。
对于《论语》、孔子、儒家来说,“人”是开始,也是目的,而“道”是手段,即使是“圣人之道”,也只是把“人不知”世界改造成“人不愠”世界的手段,无论从开始到成就,都离不开“人”。“道”是“人”行的,而非“人”是“道”行的;“道”是“人”光大的,而非“人”是“道”光大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算初步明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而人被无所本地抛掷在此世间,就是人的当下,就是人的承担,这构成了人的无所位次,而人“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才有这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才有个体的存在发展,这里没有所谓的悲剧、喜剧、正剧,没有人,无所谓天地,也无所谓人展现的舞台,又何来悲剧、喜剧、正剧?悲剧、喜剧、正剧都不过是人生“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而来的位次展现,这里所谓理智、情感的预设,没有人,又何来理智、情感?这里只有承担,人的承担,首先是对“人”的承担,由此承担,才有所谓乐、悲、情、智、观、欲等等葛藤,只有这样,才算进一步理解何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参考资料自孔圣人网www.kongshengren.cn
这句话语出《论语·卫灵公》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意思是:人能够使道发扬光大,不是道使人的才能扩大 人必须首先修养自身、扩充自己、提高自己,才可以把道发扬光大,反过来,以道弘人,用来装点门面,哗众取宠,那就不是真正的君子之所为。
这句话在儒家很重要,是论述人的意义,是儒家的根脚。
人生于世,会有一个类别的困惑,作为人类这个类别本身的困惑。
个体的人,会需要整个人类形成的整体意义,明确在天地之间的定位。单独一个人,无法形成面对天地的意义。一定是群体在天地之间、万物之中的衍化,才足以形成人的意义。
人类这个群体懂得了自强的道理,就不会产生依赖神灵,依赖命运或者运气,知道人生是有价值的,且是自己能够创造价值和幸福的。一切在自己手中。这个道理,人要懂得,这是根本。但是一个社会是否给人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机会,则是人群社会本身是否弘道的问题。
非道弘人,道不会弘人,只有人会想去弘人。而人弘人的目的,其实不是弘人,而是弘“我”。弘我,就是自私,就是不弘道,就是不出自我,就是不入天地,就是不尊重他者。人类一切的巧言令色,放利而行,其实就是因为内心走不出弘我这个误区。
个体走不出弘我的误区,人类这个群体,就走不出弘人的误区。好比赞美传统文化的人,却不努力学习;不是在弘扬传统文化,是弘扬自己的见识而沾沾自喜,口口声声说在嘴里,自己却不去有所作为的,都是巧言令色,都是心在弘我,而不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