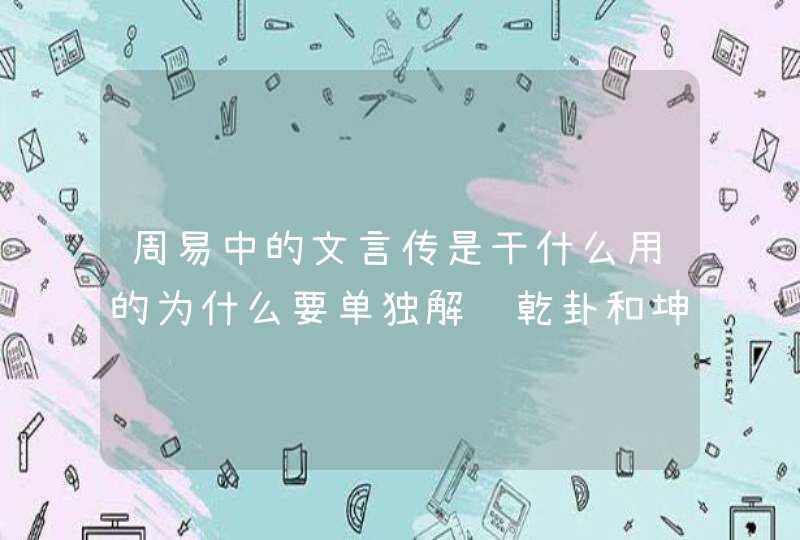世界之大,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好在我生活在一个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最好的时代,借着网络可以了解到大洋彼岸的人们怎样生活,通过**可以知道另一个半球是个美丽可爱的地方,通过书本可以懂得这世界上还有好多个民族国家的风土人情。
在这大大的世界里,我这个小小的人儿,向往着去地球的最南端――南极去看极光,向往着去地球的最北端――北极去感受爱斯基摩人的生活。
1922年,一部无声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上映,导演是罗伯特·弗拉哈迪。记录了加拿大魁北克省北极圈内哈德逊湾的伊努朱亚克附近因纽特人首领纳努克一家的日常生活。
因纽特人,也就是之前称呼的“爱斯基摩人”。影片主要介绍了纳努克与白人交易、抓鱼、捕猎海象海豹,建筑冰屋的过程。
在这片冰面上生活着一群靠狩猎为生的人,但他们却活得很无畏而潇洒,开心的活在这里,甚至不知道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更无法想象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群人生活在赤道附近,终日暴晒,皮肤黝黑。在他们的世界里,世界就那么大,大家都是那么活着,每天都在为食物奔波,吃了上顿没下顿,经常行走在饥饿的鬼门关之前这是正常的!
纳努克作为一家之主,需要为一家人的食物而奔忙。他是这个地区最好的猎手,当大冰盖封锁一百多英里的海岸,家人快饿死的时候,他必须出来寻找食物。他靠着自己的技巧成功穿越危险的浮冰,并很快找到一个抓鱼的好地方。没有鱼饵就用两根象牙诱惑鲑鱼上钩,一天下来收获不少,带回家去又能让家人饱餐一顿。
他们迁移主要靠双脚徒步旅行,冬季还会用狗拉雪橇,影片中出现了七八条狗,头狗长得很像狼,叫声也会发出狼嚎。带着这么多条狗,再加上狗原本就不是群居动物,自然免不了经常打架,头狗会受到挑战。有时候他们的旅途也会因为两狗打架而被耽搁,不能及时回到家中。
他们可以临时搭建一个露营地,选择一个深厚坚实的雪地,开始建造他们的“伊格鲁”,用舔过的象牙做刀开始切雪块儿,这样刀身会覆盖一层光滑的冰,可以切得更快一点。奈拉作为纳努克的妻子,与库纳尤一起用残雪对缝隙进行贴合。
最后,纳努克又去找了一个冰盖做天窗,用反射的阳光穿透窗户,这样里面会亮一点。建造冰屋的过程不到一个小时。看到这里我在想,非洲某些部落的茅草屋需要多久搭建完成?
他们猎捕海豹的方式,是利用海豹需要呼吸这一特点。海豹属于哺乳动物,在水下最多待20分钟,就需要呼吸一次,因此在冰冻的海面上,它们会给自己留下一个小孔呼吸。纳努克正是抓住了这一特征,守在小孔附近,等待抓到海豹。抓到之后与海豹进行力量的抗衡,随后家人赶到,在其他力量的支援下,海豹很快筋疲力尽,窒息而死,再挖个大口把海豹拉上来,他们一家人又能饱餐一顿。
因纽特人直接生吃海豹肉、海象肉、鱼肉,所以才会被印第安人讽刺为“爱斯基摩人”。或许是那个年代没有烹饪的条件,现在的因纽特人也喜欢吃生肉,因为他们觉得熟肉是对肉的一种侮辱。而且生肉更有嚼劲,还能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
他们像原始人一样活的开心自得,哪怕每天为食物而奔忙,还是开心无邪地笑着。观影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他们夫妻之间会不会打架?会不会像现代社会中似的,有外遇?奈拉每天早上都要给丈夫纳努克用牙咬靴子,因为经过一夜,这海豹皮做的靴子会变得又僵又硬。看上去他们挺恩爱的!(是不是有点“小人之心”了?)
他们对孩子也很好,纳努克偶尔教教大儿子艾力如何拉弓,给他做一个小冰熊让他练习。赤裸双手的小男孩儿做这项寒冷的运动,很快就双手冰凉,纳努克就捂着他的手贴到自己的脸上暖着。
奈拉照顾着他们的小婴儿,不到4个月的孩子,光着身子,每天背在妈妈的帽兜里。在与白人的贸易市场上,奈拉将自己的小婴儿放到狗崽堆里,让他们一块儿玩,4个月的小孩子已经会坐了?而且还搂着小狗崽的脖子,看上去他还挺享受的。而且每次纳努克打到食物,奈拉吃完都会直接递给小婴儿生肉,他接过来直接塞嘴里,完全不像4个月大的孩子,更不会像现代社会的孩子一样,需要每天追着喂饭。每天早上奈拉都会摩擦鼻尖,以表示对孩子的疼爱。
夏天的时候,冰面全化了,听说附近有海象出没,一群人就会每人划一条独木舟,赶往那里。遇到一群熟睡的海象,有个“哨兵”醒着,不过他们蹑手蹑脚地靠近,再加上海象视力不好,等它发出危险信号时,总有一只海象动作慢一点,被逮住。然后一群人拉着它,使它直到窒息。虽然海象被称为“水下的老虎”,但是离开水,它们还是孤立无援的,尽管海象群发出愤怒的声音,对着这群“野蛮人”怒吼,海象的配偶更是生气。但在饥饿鬼门关面前,这群人是不会松手的!猎捕成功之后,他们直接开吃,因为太饿了,根本等不及带回家。
1922年,只有无声机问世,纳努克在与白人的贸易中,白人向他展示了留声机的原理以及如何把声音“装”进去,可爱的纳努克拿起碟片就开咬。
影片最后,我惊讶于它的拍摄难度,在北风呼啸的状态下,摄影师是怎样拍到如此珍贵照片的?而且每每想到我的手机在冬天里总是冻没电,这个摄像机咋没事儿呢?而且像素还这么清晰?
纳努克不懂为什么导演要离开这个地方,这群因纽特人勇敢而纯朴,如果有剩的食物会分给邻居或者部落中其他人,他们中没有货币交易。虽然与白人之间也有贸易,但他们只是物物交换,他们将一年下来打到的北极狐的皮毛、熊皮换来白人的刀子和各种颜色艳丽的糖果。可在我看来,这真的是不平等交易!
随着时代进步,现在的因纽特人已经住上了木制房屋,也有了地下热水管道,还开上了小汽车,完全进入文明社会。毕竟1922年已经过去96年了!这部影片评分86,而且过去这么多年,依然有人爱看,因为它记录了那段历史。可能因纽特人的后代也感谢这部影片吧!
――我是素颜姑娘不怕雨淋
写于2018年4月18日
有。《北方的纳努克》是由罗伯特-弗拉哈迪执导的纪录**,在剧中纳努克有后代并且有大大小小三个孩子,该片以爱斯基摩人中最出色的猎手“纳努克”为主角,展现了他们捉鱼、捕猎海象、建筑冰屋的场景,整部剧情节环环相扣,深受群众喜爱。
是真实的。
纪录片美学观的奠基者:维尔托夫、弗拉哈迪。其中维尔托夫开创了"**眼睛派",提倡镜头如同人眼一样"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反对人为的扮演,甚至反对带有表演的影片(故事片)。而弗拉哈迪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却是由纳努克"真实"扮演而成,最后由现代文明重返原始生活的纳努克甚至因为缺乏过冬食物而死。同为纪录片的先驱,他们的风格却迥异,这也成为日后纪录片流派纷争的源头。
弗拉哈迪本身没有足够的资金,且认识有问题。弗拉哈迪本身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提供一家人的物质,且局限认识纳努克是一个优秀的猎人,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下供给到一家人的资源。《北方的纳努克》是由罗伯特·弗拉哈迪执导的纪录**,由纳努克等主演,于1922年6月11日在美国上映。该片以爱斯基摩人中最出色的猎手纳努克为主角,展现了他们捉鱼、捕猎海象、建筑冰屋的场景。
浅析弗拉哈迪作品《北方的纳努克》与《亚兰岛人》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的诞生始于纪录片的创作。以下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浅析弗拉哈迪作品《北方的纳努克》与《亚兰岛人》,欢迎大家阅读!
浅析弗拉哈迪作品《北方的纳努克》与《亚兰岛人》
“搬演”又称情景再现,对于纪录片来说,搬演就是使用演员、置景、道具等手段来表现某一个曾经(或可能)发生过的事件。“在纪录片中使用搬演的手段与剧情片有所不同,尽管搬演避免不了虚构,但是对于纪录片来说,这样的虚构必须被纳入非虚构的范畴,或者至少不与非虚构的原则发生抵触”。
搬演在今天在我们的很多纪录片,尤其是主流媒体的电视专题片或者宣传片中已经司空见惯,比如央视近年比较有影响力的纪录片《故宫》,北京电视台的《档案》栏目,崔永元的《**传奇》系列等等,本文回到纪录片的起始阶段,从人文关怀角度探讨弗拉哈迪对其作品《北方的纳努克》与《亚兰岛人》两个影片的“搬演”处理。
虽然两个影片都是基于对客观真实存在的事件的还原,但是《北方的纳努克》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虽然拍摄的都不是现实生活中进行时态的事件,弗拉哈迪赞美的不是爱斯基摩人当时的生活方式,而是他们记忆中的往昔传统。《亚兰岛人》也一样是搬演亚兰岛上居民曾经的生活状态,都具有一定的记录价值和社会学研究价值。而之后有不同的评价和待遇,是因为影片制作过程,导演拍摄动机及两个影片所具有的审美价值等等因素决定的。弗拉哈迪拍摄《亚兰岛人》同样延续了《北方的纳努克》的的拍摄手法,而且从制作手法上已经超越《北方的纳努克》,戏剧性也更强,但是影片的社会影响无法与《北方的纳努克》相提并论。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比分析:
1、拍摄动机对比:主动审视和被动审视
弗拉哈迪拍《北方的纳努克》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个人情感,如他自己所言:“我执意要拍摄《纳努克》,是由于我的感触,是出自我对这些人的钦佩,我想把他们的情况介绍给人们。”他这样写道:“白种人不单破坏了这些人的人格,也把他们的民族破坏殆尽。我想在尚有可能的情况下,将他们遭受破坏之前的人格和尊严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个主观感知客观真实的过程,是主观艺术审美价值取向的客观表现。弗拉哈迪已经被爱斯基摩人感动,所以才会驱使他几次探访北方,深刻了解了爱斯基摩人过去和当时的生活状态,拍摄时间长达10年,可以说这是一部时光堆积的不朽纪录,是主观的在纪录。而且弗拉哈迪和纳努克在这一过程中关系由拍摄者和被摄者转变为有着深厚友情的朋友关系,整个片子更有人性的主观的东西在里面,更具有亲切感,更使人感动。
而弗拉哈迪拍《亚兰岛人》是有**公司出资赞助的被请去拍摄的一部“远程旅行纪录片”,是被动的去感知客观真实,是一种纯粹的“他者”进入。而且很多场面就是纯粹的搬演,虚构的成分非常浓,比如《亚兰岛人》中一个岛上的男性原住民纹身一段,男性原住民这一“表演”是被导演的,而且是有片酬可以拿的,而在《北方的纳努克》中,纳努克虽说也是在表演,但是他的主观情感表露要比《亚兰岛人》中男性原住民的表演真实,亦或说朴实,因为他们没有金钱关系,创作者和被摄者的关系纯洁的多,而后者就是一个雇佣关系的影像体现,是简单的被摄者和拍摄者的关系,和我们今天的导演和演员的关系是一样的。《亚兰岛人》最后成为当地居民吸引游客的工具也就不奇怪,两部影片的拍摄动机不一样,具有的审美价值也就有所区别。
2、表现形式分析:个体表现和群体表现
《北方的纳努克》表现的是以纳努克为主要拍摄对象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主要通过纳努克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体来表现。纳努克是焦点,叙事的线路比较清楚,主要以纳努克为主线。他以个体代表了爱斯基摩人这一特殊群体。所以在影片叙事上它的结构是密集的,人物性格刻画相对容易些,所以塑力了纳努克这一勇敢男子汉形象。而《亚兰岛人》是以一个群体为主体对象来展开,叙事的线路不明确,焦点模糊,结构散乱,不能突出表现,人物形象立不起来,缺少像纳努克那样的一个精神象征。
3、拍摄时间比较:几近10年磨一剑和三年拍摄的结果
《北方的纳努克》前后制作长达10余年,《亚兰岛人》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从时间上就可以判断两部影片的积淀程度,《北方的纳努克》像一坛老酒,品起来回味无穷,而《亚兰岛人》只能算是一瓶啤酒,喝起来让人涨肚子罢了,同样是酒,但是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弗拉哈迪拍摄《北方的纳努克》,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不是科学的精确纪录,而是对现实生活充满诗意的再创造。弗拉哈迪对现实是持积极参与的态度的。因此,弗拉哈迪是浪漫的诗人而非科学家。他需要的是摄影机前的真实,是拍摄结果的真实。这是弗拉哈迪的真实观。比如他曾对纳努克说,如果拍摄捕猎海象,“在影响拍摄的时候,你和你手下的`人可要放弃猎物。你要知道,我要得是你捕海象的镜头,而不是它的肉。”
此外,还有一个说法,据说那个著名的猎取海豹的场面里,纳努克从冰洞里拖出的海豹其实已经死了多日。整个场面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尔·尼克尔斯的 《纪录片导论》中这样描述弗拉哈迪和爱斯基摩人纳努克的关系:“它以一种爱斯基摩人自己并不十分愿意接受的方式展示了爱斯基摩人的文化,它代表的是弗拉哈迪的赞助人雷福林·福斯的利益。”
而《亚兰岛人》更是遭到同为纪录**大师的格里尔逊的公开质疑:“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中,弗拉哈迪为什么无视亚兰岛居民在困苦中挣扎的社会背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亚兰岛人》和《北方的纳努克》在人性关怀程度上的差距,再一次说明功利性强的艺术作品是很难超越主观的,人性的作品的,毕竟人是影片恒久不变的主题。
其实,在弗拉哈迪拍摄《北方的纳努克》的年代,当地的爱斯基摩人捕海象已经不用鱼叉,而是用步枪。为了拍到更为原始的场景,纳努克才用他爸爸的方式猎捕海象。弗拉哈迪在后来的《摩阿拿》、《亚兰岛人》和《路易斯安娜州的故事》等影片中一再重复这种拍摄方式,让人们用父亲或祖父的方式表演生活。
有人据此斥责弗拉哈迪“做假”。弗拉哈迪却认为在艺术创作中,创作者的行为方式是积极主动,而不是客观冷静。这就要求把非虚构的生活场景同想象和诗意完美结合。摄影机前的生活只有合理干预才是更真实、更合理的。这种思想观念对后来的纪录片创作影响深远。
《北方的纳努克》影评
第一次上纪录片课,看的第一本片叫做北方的纳努克。黑白默片,字幕解说。常常说电视比**平民,就是因为看**时,只有银幕是发光的,人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那儿,无法分心做其他事,当然,除了睡觉(这里特指在**院,幼年的我常犯这种阶级错误)。而电视摆在那儿,随意性很大,看的人可以做别的事,吃饭喝水打牌。所以如果从开头就吸引了人,那么就可以将人的目光吸引在电视上,从而无心做其他事。
本以为很枯燥,不料从开始就被吸引,如同老师说的,纪录片开头就要吸引人。我错过了开篇,从纳努克坐上船然后下船那里开始看,“下船”便是那个纪录片历史上公认的经典长镜头。老师说如果由几个镜头完成,会让人不免怀疑那艘船是不是真的可以装那么多人,想想是很有道理,可是我也有点小小的怀疑,是不是弗拉哈迪不经意的举措,也许他认为一个长镜头可以搞定的不需要一个一个地剪。下个船而已。(学术研究者看到不要打扁我。)
纳努克的确是个出色的猎手,他穿越浮冰的技术一流,独自一人,独一叶扁舟,在浮冰重重的海面自如游走,看似平静也许暗涌不断,也许暗藏在水下的冰峰可以轻易将他阻挡。即使徒步穿越,手持一细长棍就能探测虚实,若是我等,恐怕只能望而兴叹了,甚至会盲目跌落水中,葬身冰冷海水之中也许不忘感叹自己为何不生在爱斯基摩人之中。
捉大马哈鱼,背景音乐也配的极好,没有诱饵的垂钓,纳努克有节奏的抖动手腕,如正在弹奏。捕上岸的鱼直接用嘴咬死。
值得一提,爱斯基摩人处在古代文明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喜欢用嘴唇以及牙齿去试探。比如用嘴将捕得的鱼咬死,面对从未见过的黑胶碟唱片,他也用牙咬一咬;孩子们争夺海豹鳍也是用牙齿紧紧咬住的你来我往生拉活扯;早晨起床妻子为丈夫用牙齿咬软冻僵的靴子。
他们表达情感与内心的举动直接而单纯,如同婴孩——我见过许多抓了东西就往嘴里送的小孩子。
最喜欢他们与白人交易的那一段,他围绕着唱片机,拿起唱片咬一咬,看一看,再咬一咬,脸上的笑纯粹的一下子就感染了我。纳努克的孩子们吃着白人们给的蛋糕点心吃到撑,不得不喝下一口植物油润肠,腼腆地看着镜头笑着咂嘴,仿佛连油都是可口的。这一段的背景音乐也配的极好,轻松跳跃如同卓别林的**。
平行蒙太奇的运用在建造“伊格鲁”(即爱斯基摩人居住的冰屋。)时表现的很好,一边是大人们建造冰屋,一边是孩子们“滑雪”,每滑一次,爸爸的屋子就已经升起大半。他们是充满智慧的,因为懂得如何采光,一切纯天然。
而与他们单纯可爱对立的是,捕猎时的凶猛。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他们捕猎就不单纯不可爱了,只是原始的人性直接表现出来,如同兽类,但可以理解。匍匐前进,向一群熟睡的海象趋近,只有一只“哨兵”,还是发出了警报信号。但慢了一步的,不幸就被叉住,就是这一段让我觉得,“落单”这个词的深刻含义,同伴们都得以逃脱,只一个深陷危险之中,眼前的是同伴的回望,而身后却是猎人紧紧不放的绳索,金属的钩叉在身体里的刺痛提醒着自己的恐惧。虽然海豹有两吨的体重,但还是敌不过人类的力量。同伴无效的努力救助,最终还是没有救回落入人类手中的落单海象,终是死了。纳努克和同伴费力的将它顺着海浪拉上岸,即使饿着肚子,对食物的强烈欲望使他们将两吨重的海象,剥皮,肢解,然后用满足的表情啃食割下的肉。是的,在现代人看来无法理解的吃生肉。
如此的搏斗还有最后的捕海豹,而这次落单的是纳努克,当然也是片中另个著名的长镜头。他只身一人,与海豹拉锯般的拉扯,如果不是看到前因后果,就很像滑稽录像,纳努克用各种姿势拼命拉住他们一家的食物,而食物为了生命拼命的挣扎。当优势者落单时,只需发出求助信号变有同伴前来帮助,纳努克打着手势向同伴求助,人多力量大便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两个落单,结果却不同。海象丢了命,而纳努克得到了食物。
另个比较震撼我的镜头是,拉雪橇的狗们,闻到海豹的血腥味,露出了它们祖先狼的本性,龇着牙,表情贪婪凶狠。与它们晚上在伊格鲁之外满身落雪的傻傻的样子,实在不同。都是有本性的吧,人和兽类。
大自然的弱肉强食就是自然法则。
这是弗拉哈迪第二次进入北极拍摄,第一次拍回的胶片因为一个烟头化为灰烬,也似乎是天意让他尽善尽美。当再次回到爱斯基摩人之中,不仅与他们朝夕相处获得了信任使得纳努克一家在镜头前高度自然,而且完善了之前的不足。有说弗拉哈迪拍这本片是因为目睹了工业革命给自然带来了野蛮的伤害,本着让人重温古代文明的意图。
值得一提的一点是,对于这本片,反对的人,一是因为:片中有搬演和主观干预,与现实不符,比如当时爱斯基摩人已经不用鱼叉而是用步枪捕猎;纳努克一家的起床是“表演”的结果;因为照明问题,只能将伊格鲁削去一半。二是因为他们认为弗拉哈迪不关心社会,仅仅醉心与异域风情。
我却认为这样的理由若是当时,是可以引起共鸣的,但在现在这两个所谓“不好”,根本不值一提。纪录片奇妙的,它要求真实却可以用假来表现创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它可以反映社会也可以表现创作者的内心。
关心国家大事社会时事政治,或者只顾内心理想偏爱坚持,管他的。
;以上就是关于来自地球最北端的故事全部的内容,包括:来自地球最北端的故事、北方的纳努克有后代吗、人类溯源纪录片里的人都是真实的吗等相关内容解答,如果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